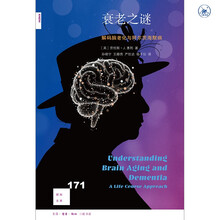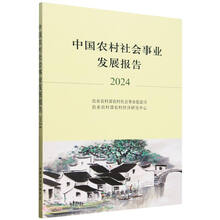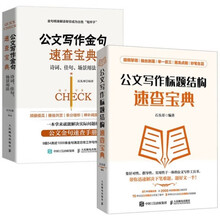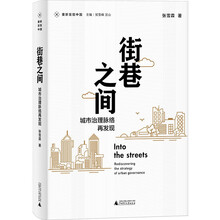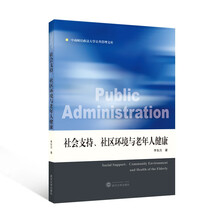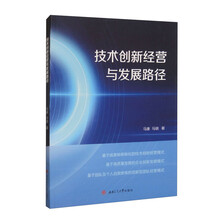《国际商事惯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国际商事惯例裁判标准的发现
承前文所述,已有的大多数文献在研究商事惯例时,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商事惯例在裁判中的裁判标准问题。换言之,法官或仲裁员在进行裁判时,援引商事惯例对于为何要适用商事惯例,判断商事惯例的司法标准以及在商事惯例之间产生冲突应当秉持何种标准进行判断存在模糊的认知,因此在研究商事惯例的地位时必须解决该问题。在此思路指引下,笔者试图通过梳理典型案例中外国著名法官对商事惯例进行裁判时的说理过程发现国际商事惯例在司法中应当遵循的判别标准。
在“通用再保险公司诉芬兰芬尼亚保险公司”案中,英国王座法院的法官认为,取消再保险修改要求的惯例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某种行为模式已然充分明确和明晰,以至于参与同样交易的当事人有理由认为必须同意这种行为模式时,才能使得这种行为模式作为商事惯例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后果。当事人单方面的相信不足以使得这种行为模式获得商事惯例的地位。①这就要求出庭作证的专家证人之间的证词高度一致,换言之,如果商事惯例的适用将会排除交易当事人的主要权利时,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商事惯例的适用过程,必须将当事人的交易环境和交易意图纳入到确定商事惯例的考察范围之内。②再如,在“利比亚阿拉伯国家银行诉英国银行家信托公司案”中克里斯托弗·斯托顿(Sir Christopher Staughton)大法官在审理后认为:“虽然CHIPS是欧洲美元业务下普遍使用的业务系统,但是如果想要构成一个否定性的免责条款以排除原告方的一项权利,以上的事实显然是不够的。我需要更多的证据表明为什么合同的一方要同意这么做,而并不是他从来没有行使过这项权利。换言之,我必须得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已然建立起对于涉诉交易模式的充分信任,然后才能使这种做法产生法律约束力。但很明显,现有事实证据并不足以满足上述条件。”①在该案中法官强调了将当事人交易意图作为商事惯例进行裁判的核心裁判标准。因此,笔者初步认为,任何国际商事惯例在适用时必须要考虑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要通过案件中呈现出的证据准确推断当事人对案件可能涉及的“国际商事惯例”的接受情况。认为国际商事惯例具有自治性,因此就不考虑当事人的接受而直接适用的观点显然很难成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CISG作为最为权威的国际法律文件,其对惯例的规定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重要依据。根据CISG第9条的规定,都有“同意”这一明确的限定语。不同的是第1款的同意是基于缔约双方当事人的明示同意,而第2款则是在商事惯例为从事同样特定贸易的商人广泛知道和经常遵守的事实状态下,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商事惯例的内容的前提下,推定当事人默示地同意商事惯例的内容,进而产生法律约束力。同时CISG为了解决当事人的意思在具体的案件中难以探知的难题,规定了理性当事人的标准,根据CISG第8.2条的规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应按照一个与另一方当事人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应有的理解来解释”。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惯例必须和当事人的交易意图进行相互印证式的理解。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不难发现,商事惯例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进而应当由裁判机关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明示或默示地同意商事惯例对他们产生约束力。因此,在进行裁判的过程中必须通过案件的客观证据,从一个理性第三人的角度理解当事人的意图,发现当事人按照商事惯例的行为的真实意图时,通过对意图的理解决定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商事惯例。我们发现,相对于成文法律,商事惯例的裁判往往更依赖于案件各种事实以及细节的再现。没有这些案件事实细节的阐明,就无法查明当事人对惯例的真实态度,商事惯例的适用也就无从谈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