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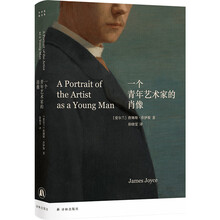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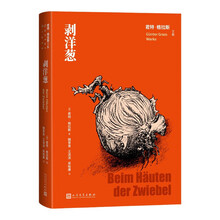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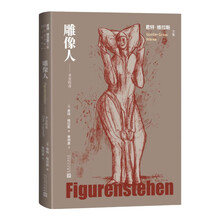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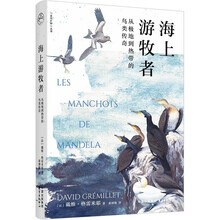

1. 2020年龚古尔奖瑞士评选,勒诺多读者评选,巴黎政治大学读者大奖文学类。
2. 一场针对花龄少女的骗局:困窘的家庭、缺席的父母、成名的诱惑、男性评审团的秘密……
3. 献给所有的不完美受害者,以及成千上万与过去的羞耻对抗的女孩。
4. 只有文字才能疗伤。《倾覆》是关于女性友谊和命运的成长小说,它给那些曾不顾一切追梦的女孩创造了一次与过去、与自己和解的机会。
5. 受侵害女性的突围:作为曾经的猎物,此刻决定揭开伤疤,用成长的代价和痛苦换来一次迟到的救赎,用勇气对抗生活的不公。
1984 年,出身普通却梦想成为舞蹈家的13岁少女克莱奥掉入了恋童癖基金会的陷阱,被精神控制后成了他们的“帮凶”,帮他们寻找其他合适的“猎物”(13一15岁的女孩子),发现真相后成功脱。
2019年,一项针对该基金会的调查在网络上展开基金会背后的黑幕逐渐暴露在公众视野下。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克莱奥愿意打破自己平静的生活,以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说出真相吗?
节选一
一位颇有话语权的评委看了她的资料,说想见见她!卡蒂向克莱奥母女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并承诺,她会和克莱奥一起去见他。
来到约定的地点,开门的男子看起来比父亲还要老。他叫马克,说话时像校长一样严肃:许多年轻的女孩子一听说过了初选都异常兴奋,尽管卡蒂一直说你很有潜力,但更重要的是,最终的人选,除了才能之外,还得具备其他一些东西。
你觉得自己有何特别之处?
我的跳跃,我的旋踢!还有……我不怕辛苦。像纽约表演艺术高中的学生一样每天练舞六个小时,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你的资料看起来很诱人,但本人少了一些活力,或者说有点儿学生气。
听到这儿,卡蒂身子倾向克莱奥,温和地提醒她:听懂了吗?学生气,就是说太乖了。
马克补充:对,有点太乖了。
克莱奥的心在狂跳,觉得有些透不过气来。随后又沉了下去,仿佛在胃部形成了一个黑黢黢的大水塘。完了,以后不会有人再讨好她,不会有人关注她,通向巴黎的大门也就此关闭了。
卡蒂安慰她:基金会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是一个团队,大家齐心协力,就是为了找出你身上与众不同的某个地方。
听着自己颤颤巍巍地说没什么特别之处,语气稚嫩如同婴儿,克莱奥充满了挫败感,暗自生气。自己的长相真没什么特别的,刚出生时,母亲还把自己和另一个婴儿搞混了。好在自己身上有个胎记,克莱奥边说边指着大腿处。
这有点意思。好吧,你够胆量展示一下吗?
听到“够胆量”这么过时的词,克莱奥差点笑出声来。随后,她很配合地解开了裤子的纽扣,用手指了指三角裤边缘处的那块褐色胎记。
卡蒂对她做了个手势,让她重新穿好裤子:谢谢你抽空参加面试,现在可以走了。
回到车里,卡蒂又给了她一百法郎,还有一个方方正正的礼盒:下一次见评委时,这个礼物可以给她带去好运。里面是圣罗兰的“鸦片”,和卡蒂用的一样。她眨眨眼:这样我们就有同样的味道了。
为什么能得到一百法郎呢?因为灵机一动提到了自己的胎记,还是因为脱下了自己的长裤?她甚至连舞都没跳啊!
因为胆量,卡蒂回答,因为你没有被吓到。对于一名舞者而言,能够临场发挥至关重要。评委们会不遗余力地给候选人制造麻烦,你得有足够的胆量,就像在舞台上一样。
听到克莱奥说一切顺利,父亲很是自豪,并未过多询问。隐瞒另外一种生活的出现,对关心自己的长辈说谎,这居然令她感到些许兴奋。这样的秘密令克莱奥有些飘飘然。她已不动声色地超越了自己的父母。卡蒂还对她说,和评委见面的那间公寓将是她的秘密花园,她可以在那里起飞,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入睡之前,她小心地嗅着“鸦片”的香味,一股诱人的甜香。
危险的气息有时很柔和,就像眯着眼打盹的野兽。
节选二
一个周五晚上,在准备晚餐时,克莱奥突然对她说:我想跟你说件事。说完,她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也不是什么急事。最后,她改变了主意:今天有些累,我想早点睡,以后再说吧。
几天后,她们坐在“美丽城”最喜欢的一家餐厅里,克莱奥重复道:我觉得有一件事必须告诉你。
坏事?很坏很坏的事?拉腊调皮地问。但她又害怕起来,恐惧就像被突然放进热水里的水银温度计,指数疯狂攀升。她接下来会不会说,她和那个染了头发的舞者有过一段故事?
回到公寓,两人面对面坐在厨房里。拉腊想象着分手的场景,对方摊牌的时候没有抱着她:“很抱歉,但是……”
好吧。
我的父母并不是你口中的弱势群体。但在生活中,在工作中,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死死抓住,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餐桌上的每次谈话几乎总是以“就这样吧”作为结束语。他们对我没什么要求,只希望我能平平安安的。
冬日里,克莱奥每周六下午会去林畔丰特奈的溜冰场,那里总放金·怀德1 的歌,她就在歌声里不停转圈。男孩们喜欢跟在女孩后面,炫耀着自己的技术。女孩们看着他们,各自卖弄,希望引起他们的关注。到了春天,她周六会和女友们去克雷泰伊阳光城购物中心,流连于各个店铺,试试这个,试试那个,最后却什么也不买。有时候,她们会顺手偷些小东西,相当容易。
日子就这么过去,平淡无奇,仿佛永无终止。只有在斯坦老师的舞蹈课上,一切才变得有趣,在那里,她重新发现了自己。
二月的某一天,在MJC 舞蹈中心,一个女子主动和她搭话。女子打扮精致,年纪和她妈妈差不多,可能还年轻些。克莱奥不愿提女子的名字,只说女子选中了她。为什么是她呢?也许因为她是班上最小的学员吧。
她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世上存在一个伽拉忒亚基金会。为什么不可能呢?叫伽拉忒亚有什么问题吗?它能帮助那些最有才华的少女实现梦想。那个女子教会了她很多东西。克莱奥跟着她去巴黎玩,去高档餐厅吃饭,去逛古董店,逛娇兰专卖店,逛书店,看经典电影。母亲见过她,对她印象也很好。
拉腊打断了克莱奥:你在讲什么?你在讲自己的初恋吗?你爱上了一个年长的女人?当时你几岁?
克莱奥没有回答她。陆陆续续地,她又讲了几个零碎的场景,讲述的过程中,她显得很疲惫:一间散发着霉味的公寓,在巴黎十六区的某条街道上。在里面见了几个男人,基金会的评委,有四个还是五个,还有同等数量的小女孩。午宴时,女孩之间并无任何交流。零交流。她们彼此间是竞争关系。大家各施所长,只有最好的才能胜出。优胜者能得到什么呢?两三张大额纸币。公寓的走廊两边,还有几间卧室。
你当时几岁了?拉腊再次问她。
她们坐在客厅破旧的沙发里。时值五月,窗外夜色已黑,空中悬着一轮明月。克莱奥光着脚,膝盖抵在胸前,低头玩着自己的脚指头。
之前拉腊每次问起,克莱奥总说童年的记忆都模糊了,原来并非如此,那段记忆只是被她锁在了心里的某个抽屉里。现在,这个抽屉展示在拉腊面前,里面散落着不堪入目的东西,乱七八糟的词语,脏话,令人彻夜难眠的焦虑、羞愧。
那次之后,克莱奥开始整夜整夜地胃痛。其实胃并没有什么毛病。突然之间,一切变得毫无意义,她不知道如何开口说话。她当时没有说不,她同意了,可是具体同意了什么,她到现在还是不清楚。你当时到底几岁?拉腊再次发问,喉咙里如有一团火在烧。
克莱奥摇了摇头:“这不重要。”
克莱奥屈服了,就像拉腊鄙视的那样,员工无条件服从老板的命令。而且她还成了帮凶。初中时,同学们谈到将来要做什么,聊到最后总会加上这么一句:别净想着做梦。当时的克莱奥却鼓励她们去做梦。对于拉腊这样出身的人来说,有自己的梦想也许稀松平常,例如在舞蹈学校实习,去学网球,当翻译家,成为设计师,等等。
去过那里之后,那些女孩再也没有去学校操场找过克莱奥,仿佛她们都签下了某种保密协议。
最令她痛苦的,是没有人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克莱奥是唯一去过那间公寓的人吗?还是说每个去过那里的女孩最后结局都和她一样?她几乎可以把其他女孩都忘了,除了贝蒂,她完全忘不了这个女孩。
贝蒂的母亲缺钱,贝蒂也老说家里没钱。她自己设法打听到公寓的地址。但克莱奥没有阻止她前去。她见过贝蒂推销自己,夸耀得过的奖牌,给对方留下联系电话。克莱奥就在一旁听着,什么也没做。
克莱奥推开了拉腊的手,说自己不值得安慰。
克莱奥,告诉我,你当时到底几岁?拉腊又问。
两人躺在床上不再说话。克莱奥依偎在拉腊背上,很快就睡着了。
大多数见过她们的人都以为克莱奥的年纪比拉腊小。拉腊第一次看到克莱奥笑时,觉得她露出的牙齿就如小女孩的一般细密整齐。现在看来,这个女孩仿佛一直活在十三岁的年纪里,永远被困在了里面,走不出来。
洛拉·拉丰用生动的细节再现了职业舞者幕后的生活,揭示了表演和闪光灯背后的社交鄙视。汗水和眼泪不被看见,唯有舞者的身体和美貌被消费着。
——《每周书报》
洛拉·拉丰的新作讲述了年轻女孩在特定情况下被成人骚扰虐待的恐怖。
——《时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