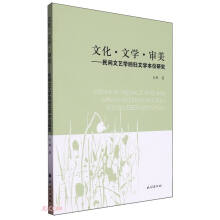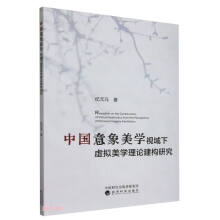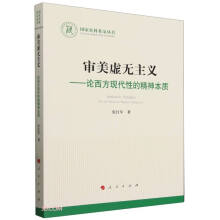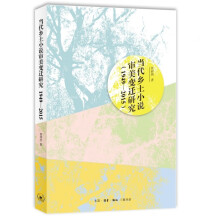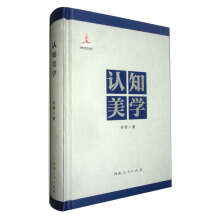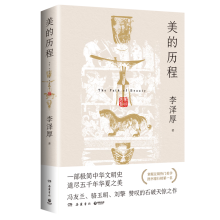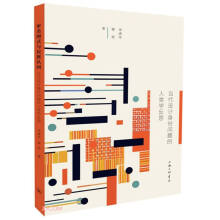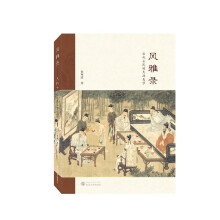《美学(修订版)》:
基于存在论的现象学的方法是发现审美意义的根本途径,审美体验获致审美意象——现象,审美的本质即审美的意义就在这种审美体验中获得。
现象学认为理解事物的本质必须把现实观念“悬隔”或放在“括号”里,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这种现象学的方法应该适用于审美体验,甚至可以说审美体验是典型的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的形式。要获取审美意义,首先要进入审美体验,或者说对现实意识进行“悬搁”并进行“现象还原”。因为现实经验的对象是表象,而非现象,它不是“实事本身”。审美体验就是要把表象“还原”为现象。在这个时候,要把现实意识和现实观念排除,以保证审美体验的纯粹性。这一步的任务与现象学的“悬搁”相似。在此前,我们还处于日常生活的现实体验之中,还没有进入审美状态。必须超越日常体验状态,屏除现实意识,把现实观念“悬隔”起来,直接面对审美对象。这就是一种带有直觉性的审美体验。但审美并不是一种先验性的“还原”,而是对现实体验的超越,是审美理想对现实体验的突破和提升。如何摆脱现实意识,进入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一个审美意识发生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审美理想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审美理想不是别的东西,乃是人的潜在的自由要求,它来自存在的召唤.是生存的超越性的冲动。它在具体的对象的刺激下,从无意识领域中发生并且转化为审美理想。审美理想是审美的动力、审美的期待和审美的规范,使现实意识得以升华为自由的意识。在审美中,我们进入了一种超常的体验,也就是一种本真的生存体验。这种体验极其丰富、深刻,一言难尽,既有极度的愉悦,又有深刻的启示。审美体验中人处于自由的生存状态,获得身心一体的解放,但心理与生理、意识性与身体性尚未分离,还处于混沌未明的状态。此时自觉性的意义还没有发生,只是一种直接的、身心一体的感受。
审美体验才是真正的纯粹意识,也就是前反思的、充分的非自觉意识,它比日常经验更全面、更深刻、更切近现象。杜夫海纳说:“审美经验在它是纯粹的那一瞬间,完成了现象学的还原。对世界的信仰被搁置起来了,……说得更确切些,对主体而言,唯一仍然存在的世界并不是围绕对象的或在形相后面的世界,而是——这一点我们还将探讨——属于审美对象的世界。”这个非现实的审美对象正是“现象”:“那个非现实的东西,那个‘使我感受’的东西,正是现象学还原所想达到的‘现象’,即在呈现中被给予的和被还原为感性的审美对象。”审美体验具有丰富内涵,是审美意义的所在。审美体验与现实经验相区别,是另一种体验方式,从意识论的角度来说,就是另一种意识类型。要进入审美体验,就要求摒除经验意识,也就是把经验意识“悬搁”,放弃对审美对象的现实观念。比如对一朵花的审美体验,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对它的欣赏中去,不去想它的非审美意义,包括它的植物学知识、商品价值、有用性等。这样就使花成为审美对象,或者说花由表象转化为审美意象,主体也就进入审美体验。这个过程相当于现象学的“现象还原”,也即使现实意识变成审美意识,使对象从表象变成现象(审美意象)。我们要真切地抓住这个体验,让审美的意象自动呈现,这就是现象。
接下来就是所谓本质还原,即胡塞尔所说的本质直观。通过深度的审美体验,就可以把握“美”的本质,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前一个过程即审美体验的继续和深入。在审美体验中,世界作为现象而非表象呈现,这也是“本质”的显现,现象即本质。所谓美的本质就在审美体验当中,就在审美现象(审美意象)当中。审美体验就是美感,审美对现象的本质把握不是通过知性而是通过美感实现的,那个最使我感动、最启发我的东西就是审美的本质。这就是说,美感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感受,而是现象学的本质还原的“现象学剩余”,那个让我激动难忘而又似有所悟的东西,就是所谓“美”。比如我们阅读《红楼梦》,感慨万千,我们痛惜宝黛爱情的夭折,悲悼大观园女性的命运,思考大家族的兴衰,其中审美本质何在?就是那种我们对人生命运的痛苦体验,就是那种不可磨灭的对自由的执着追求。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