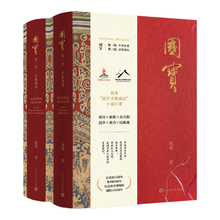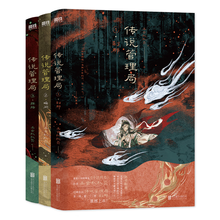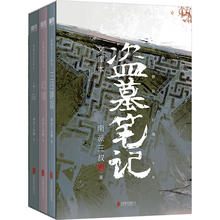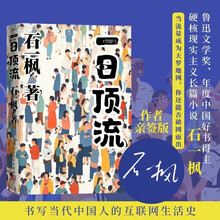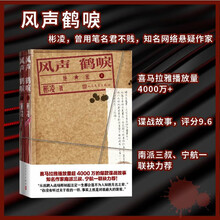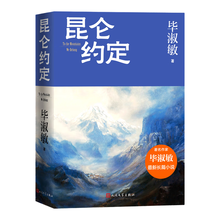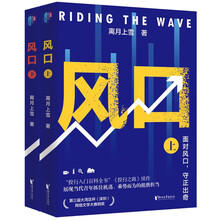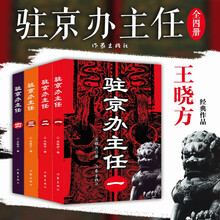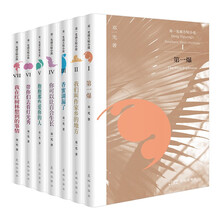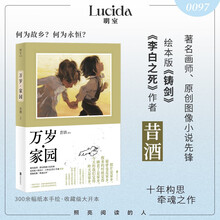《南门开》:
从历史上看,无论人与事,被朝廷关注是青史留名的最好契机。康宁博士说,其实香铺并不出众,之所以能蒙如此浩荡皇恩,缘于香铺人的手艺,即制作各种线香盘香。自古以来,焚香被认为是人与神沟通的最佳方式,无论尊卑,尤其在中国,因此制香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据载,当时正值明室中兴,天下祥和,香铺制作的线香盘香品质优良,进贡朝廷,大受欢迎,皇上龙颜大喜,便赐御笔“万世康宁”。巧的是,当时香铺恰恰只有康、宁两姓人家,于是朝廷的祝福便有了现实的对应。之后,代代相传,脂城人提到康宁,便是说香铺,一说香铺,便想到康宁了。
从地图上看,香铺的格局确似一只香炉。老牌坊直指蓝天,宛如插在香炉里的一炷高香,古朴而倔强,沧桑中透着几分吉祥。老牌坊宽十丈有余,横跨一条青石路。青石路两旁,五丈一桂,十丈一樟,老树参天,枝繁叶茂,常年香气不绝,香铺人称香街。香街呈“S”形,将香铺分为东西两半,宛如八卦的双鱼。康姓居东,宁姓居西。几百年的规矩,至今依然。
这时候,康宁博士风华正茂,思维活跃,对于故乡香铺的回忆充满留恋,甚至陶醉,以致给与会的同行留下沾沾自喜的印象。然而,康宁博士并不以为意,依然沉浸在对香铺人与事的回忆里不能自拔,且一发而不可收。在行云流水般的回忆中,康宁博士引出了一个话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与发展,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故乡香铺作为一个个案,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此前,由于康宁博士一系列人类学著作的推介,香铺的大名早为人熟知。但是,回顾历史,香铺曾经好多次出名,这一点外人未必知晓。康宁博士讲到这里,有意停顿,引起了与会同行的极大兴趣。
香铺第一次出名,是爷爷康老久用锄头刨出来的。换句话说,爷爷康老久随意一锄头,便刨开了一段人类文明史。康宁博士的说法并非言过其实,而是事实。在这段事实里,外公宁万三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当年,正是在外公宁万三的逼迫下,爷爷康老久才举起了那把生锈的锄头。说到这里,康宁博士开了一个玩笑:“由此可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搞好人际关系是多么重要!”此言一出,顿时赢得一阵热烈的掌声,可见有同感者甚众。
事实上,这个情节发生在1973年。那一年春天,“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盛行,康老久因为偷偷喂养两只下蛋的母鸡,被队长宁万三开了批斗会。批斗会上,康老久脖子上挂着那两只母鸡,看上去像个倒霉的偷鸡贼,滑稽而狼狈。鸡是芦花鸡,养得正肥,其中一只鸡在愤怒的声讨中,竟然目中无人地下了一枚蛋。蛋是红皮的,滚落在地,摔得稀碎。批斗会后,宁万三坚决割掉康老久的“资本主义尾巴”,强行将那两只母鸡没收,至于是不是上交公社,不得而知。不过,当天夜里,好多香铺人闻到,在香铺的上空一直飘荡着鸡汤的香味,久久不散。
那时候,母鸡被老百姓称为“鸡屁股银行”,调剂着乡村的M2(广义货币供应量)。康老久失去母鸡,也就失去了收入来源。恰恰这时,年幼的女儿红梅患病,哭喊着嘴苦,想吃冰糖。康老久被逼无奈,操起了门边一把生锈的锄头。当然,康老久操起锄头不是找宁万三拼命,而是到雷公湖边捉黄鳝。康老久晓得,要想满足女儿红梅的愿望,就得去合作社买糖,要想买糖就要搞到钱,要想搞到钱,只有去挖黄鳝。雷公湖的黄鳝非常有名,历来被尊为滋补的上品。即便今天,在脂城一带,能吃上正宗的黄鳝烧咸肉,依然是一件令人身心俱爽的美事。说到这里,康宁博士竟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舌根分泌出大量的口水。
按理说,康老久自小在湖边长大,捕鱼摸虾捉黄鳝不在话下。可是那天早上,康老久跑遍大半个湖滩,用锄头刨了无数个大洞小洞,竟然没有挖到一条黄鳝,只捉到九条不大不小的泥鳅。黄鳝是狡猾的,但是再狡猾的黄鳝也没人狡猾,所以康老久不相信捉不到。黄鳝跟人一样,也有喜好,而喜好恰恰就是弱点。黄鳝喜好血腥,康老久明白,要想引出黄鳝一定要有付出,于是狠下心来,咬破手指,一滴一滴,将血洒进湖边的草丛中。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