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染梦:间或戏睡乡/民国趣读·闲情偶拾》:
我刚才说过我只有在梦中才得着安宁。我在生活里找不到安宁,因此才到梦中去找,其实不能说去找,梦中的安宁原是自己来的;然而有时候甚至在梦中我也得不到安宁,我也做过一些所谓噩梦,醒来时两只眼睛茫然望着白色墙壁,还不能断定是梦是真,是活是死;只有心的猛跳是切实地觉到的。但等到心跳渐渐地平静下去,这梦境也就像一股淡烟不知飘散到哪里去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真实的我。
然而我最近做了一个不能被忘却的梦,直到现在我还能够把它记下来。梦境是这样的:
我忽然被判处死刑,应该到一个岛上去登断头台。我自动地投到那岛上去。伴着我去的是一个不大熟识的友人。我们到了那里,我即刻被投入地牢。那是一个没有阳光的地方,墙壁上整天燃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地上是一片水泥。在不远的地方,时时响着囚人的哀叫,还有那建筑断头台的声音从早晨到夜晚,就没有一刻停止过。除了每天两次给我送饭来的禁卒外,我整天看不见一个人影。也没有谁来向我问话。我不知道那朋友的下落,我甚至忘记了她。在地牢里我只有等待。等那断头台早日修好,以便结束我这一生。我并没有悲痛和悔恨,好像这是我的自然的结局。于是有一天早晨禁卒来把我带出去,经过一条走廊到了天井前面。天井里绞刑架已经建立起来了,是那么丑陋的东西!它居然会取去我的生命!我带着憎恨的眼光去看它。但是我的眼光触到了另一个人的眼光。原来那个朋友站在走廊口。她惊恐地叫我的名字,只叫了一声。她的眼里含着满腔的泪水。我的心先前一刻还像一块石头,这时却突然熔化了。这是第一个人为我的缘故流眼泪。在这个世界里我居然看见了一个关心我本人的人。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瞥,我也似乎受到了一个祝福。我没有别的话说,只短短地说了“不要紧”三个字,一面感激地对她微笑。这时我心中十分明白,我觉得就这样了结我的一生,我也没有遗憾了。我安静地上了绞刑架。下面没有几个人,但不远处有一双含泪的眼睛,这双眼睛在我的眼前晃动。然而有人把我的头蒙住了,我什么也看不见。
过后我忽然发觉我坐在绞刑架上,那个朋友坐在我身边。周围再没有别的人。我正在惊疑间,朋友简单地告诉我说:“你的事情已经了结。现在情形变更,所以他们把你放了。”我侧头看她的眼睛,那眼里已经没有泪珠了。我感到一种安慰,就跟着她走出监牢。门前有一架飞机在等候我们。我们刚坐上去,飞机就驶动了。
飞机离开那孤岛的时候,距离水面不高,我回头看那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的晴天,海上没有一丝波纹。深黄色的堡垒抹上了一层带红色的日光,凸出在一望无际的蓝色海面上,像一幅画面。
后来回到了我们住的那个城市,我跟着朋友到了她的家里,刚进了天井,忽然听见房里有人在问:“××怎样了?有什么遗嘱吗?”我知道这是她的哥哥的声音。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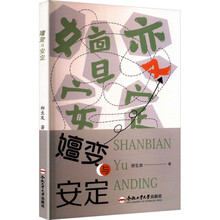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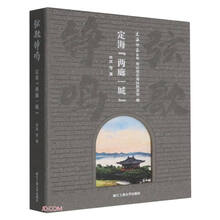
——穆旦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清)纳兰性德《如梦令》
★夜,是一块肥沃的黑土,梦的花朵盛开,红色的,白色的,黄色的,蓝色的。有的,惹人眉飞色舞;有的,梦回而宿泪仍在;有的身坠悬崖,一睁眼,死里得生而心跳未已;有的身在富贵荣华之中,觉后陡然成空。梦,是个千变万化、离奇古怪、神妙莫测的幻境,其实,它扎根于生活现实。俗话说:“梦是心头想”,一言中的。
——臧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