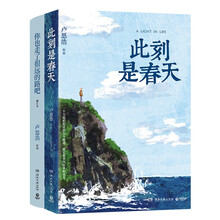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慢下来,发现风景》:
看汪曾祺的小说《八月骄阳》,直接写到老舍的形象:“这工夫,园门口进来一个人。六十七八岁,戴着眼镜,一身干干净净的藏青制服,礼服呢千层底布鞋,拄着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个有身份的人。”这是一个作家在小说中对另一个作家形象的表现,也意外勾起了我对作家如何活在后人心中这一问题的兴趣。法国的文学社会学学者埃斯卡皮有一个观点:“一位作家的形象,他以后在文学人口中出现的面目,几乎近似于他四十岁左右给人留下的那个样子。”当然,埃斯卡皮也同时提醒我们:“这只不过是统计数字,很容易找出例外的情况。”而老舍与汪曾祺,可能恰恰都在这例外之中。
我们印象中与想象中的老舍,是写《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与《茶馆》的老舍。《骆驼祥子》完成于1937年,是年,1899年出生的老舍将近四十岁。《四世同堂》写成于1948年后,《龙须沟》完成于1950年,《茶馆》创作于1956年,是年老舍年近六十。而今天的我们最熟悉的老舍的面目,当是新中国成立后、年过五十的老舍。“这个”老舍戴着眼镜,满头黑发打理得一丝不苟。这种形象也几乎一直保持到了汪曾祺的小说中——老舍“六十七八岁”的年纪。而1920年出生的汪曾祺,在上世纪80年代真正走入埃斯卡皮所说的“文学人口”的视野时,就已经年过六十,白发浓眉。两相对照起来,按埃斯卡皮的理论来判断,汪曾祺比之老舍更为“例外”一些。
我在这里勾勒两位前辈作家留在“文学人口”中的面目,并不是为了探究埃斯卡皮的观点有多少例外。因为一个作家的被形塑,受太多不可归类的偶然因素影响。比如老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前十年里,被作为“人民艺术家”为政府所褒奖。这种褒奖,使得这一时期的“老舍”成了他留在人们心目中的普遍形象。而如汪曾祺,年过花甲,才如被重新发现般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与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风潮的变动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但我觉得,除这些偶然的因素之外,也有相对必然的因素,那就是:作家的形象还与他们的作品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如何看待“写作”这件事的。按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分类,比较细致地说,老舍属于“京味”作家,而汪曾祺则是“京派”作家的余脉。尽管都带着个“京”字,但一字之差,实际上恰恰是他们写作的最大差别。
老舍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学历只相当于中专。但在当时的中国,已经算是不低的学历,属于知识分子的一员了(有一个可作参考的数字:即使到了十余年后的1931年8月,全国各国立、省立和注册私立大学学生总共也不超过四万人)。按我们一般的看法来推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北京人,老舍怎么也应该属于五四运动中人。他离这场今天被我们定义为“划时代”的社会运动近在咫尺。但历史偏偏不会按着我们的想象来,老舍偏偏在此没有留下多少踪迹。于是,我们这些后来者也直觉地把他划人到老派的北京市民的群体里去,而下意识地忽略了1919年,老舍是一个刚中专毕业的二十岁青年。对此,我比较赞同社科院学者李洁非的观点:与鲁迅、郭沫若等人不一样,在走上文学道路以前,老舍“从没有预先把自己放到救国救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心理上去,甚至走上文学道路以后很久,基本也仍然不把自己放在这种位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受过新式教育的老舍是“非知识分子”,他“承接着北京胡同世俗、安然而浅近的气质”,游离于城市另一边的惊天动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