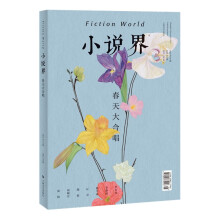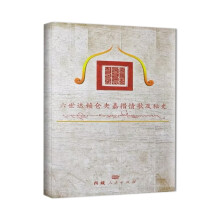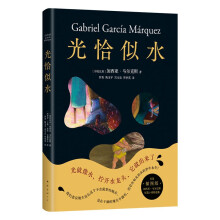村子,你是永不见到屋舍的。黄土堆积的雍山,缺乏森林,土质又不含蓄水分,在风的造化水的作用下,满处皆是冲沟,树叶状的,掌状的,花瓣状的,根系状的;黄土梁则呈平顶的,弯曲的,有“之”字形,梳篦样。人家在哪儿?只看到性崇拜的象征物:粗的细的倾斜的塔,和一个一个零散的黄土坟墓前的石板碑,以及天造地设而人并不去破坏的“孕璜含元”的黄土柱。
但沿着黄土断崖往下一看,崖壁下却是一块块场地。斜路下去,则若干人家的那窑里洞里并无断崖的。更绝的是平地掘阱,阱下辐射式地四面开窑。但这么一村一庄,却并不称作村,亦不称作庄,一律是x×营,可见这村落历史长久,均为历代的屯兵军训所致。而散兵游勇落荒为农者,现在便是雍山的土著人了。
土著人既为历代战争中天南海北的残兵败将的乌合之众,自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沿袭原籍的风俗习尚。当世几十年里,一个村为一个生产队,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人不免产生仇恨;有管制人的,也有受人管制的,更有管制过人又被人管制了的。到后来,山越来越秃,田越来越薄。不能养生,焉能问道?于是乎,居雍山下不出,狠命在土疙瘩里流汗要粮,竟不大关心了当今政府谁在台上谁又下野,只熟知立春、惊蛰、谷雨、小满,背诵“冬不冷,夏不热,五谷不结”的谚语。等到土地分包下来了,各家务各家的营生,没了直接的利害,又有了积存的粮食,人和人似乎有来有往,行门入户的礼节兴起,节时集会又恢复昌盛。酒风极凶,整夜整夜,有打着灯笼火把的一群一伙去到某某家喝个你死我活,分个雄雌。
这一天,是初夏的傍晚,天的四角高悬,柳林营村打麦场上,风把地面扫得光溜溜的,一群后生在那里打毛蛋。这是极原始的一种游戏,三年前深翻地,挖出了一块碑子,上面刻有一幅打球图。球是什么样子,看不清楚,人却是骑在马上打的。有好事者就仿制起来,规则吸收了城市人玩的垒球法。但球绝不是皮革的,也不是塑料,纯粹的羊毛缠的,便叫毛蛋了。他们全丢剥了上衣,穿条裤衩,打了赤脚,拿灰撒了四个营垒,大呼小叫地掷球。用镢把当球棒,拼足了力气去打;太激动的,毛蛋掷来,连毛蛋带棒一起打出。那毛蛋就一次又一次打到崖下的那家窑壁上。立即,有四五个人跑去要捡,尘土就腾起一团,在日里起浮。却每一次毛蛋在窑壁上反弹过来,争捡者便遗憾地站住,痴痴地看一眼那窑窗。窗上糊有麻纸,纸上贴了五毒窗花。
已经有半晌的时间了,毛蛋没有一次打进那窑窗去,连停落在窗下的机会也没有,后生们大觉气馁。后来就不再打毛蛋,吵闹着在那里用屁股掀栽石滚子碌碡做比赛,逗引着那窑门打开。眼看着夕阳已经在峁梁上坠去了一半,万泉河东边的坡上腐蚀了一片黄辉,碌碡还没有一个被屁股掀栽起来,终忍不住叫“安安,安安——”
“坏怂!”东坡洼里,小四骂了一声。
娘在窑里烧好了饭,烟熏得眼窝越发红了,一边在窑门口抹下头上的黑布帕帕拍打灰土,一边疑疑惑惑问:“你骂谁了?”
小四并不回应娘,眼睛往下看那打麦场上后生们七倒八歪地软在那里,窑门并没有开,心里倒产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感情。就扫起了碾盘上的小米,倒在笸篮里,随之将碾杆下的毛驴解了,摘了暗眼,放生了。
毛驴黑着眼在碾道里转了成千上万个圆圈,一解除苦役,并没有从斜路上下去万泉河渴饮,而倒在黄土窝里,四蹄扑打着打滚。毛驴打滚,感染了小四,小四满怀满心地涌动了英雄气概,竟也拉开马步,抬脚动手来了一通拳脚。本事显过,酣意未尽,又将那打墙捶场地的石杵子扬起砸下,“咚咚咚”地连声价响。打麦场上的后生闻声看了,自惭形秽,各自散去。小四也收了英武,将瓦盆侧靠在窑壁根,淋着半盆水洗了脸面,缩一疙瘩地蹴在碾盘上,端了耀州黑瓷老碗,吃娘做好的羊腥荞面圪坨了。
对岸的断崖壁下窑门却开了。
窑门口站着的是安安,一只脚在窑里,一只脚在窑外。那只漆一样贼亮的黑猫,已经从窑里出来,扬着前爪追扑着一只蝴蝶,追到窑垴畔上就卧下了。
小四的黑瓷老碗挡住了脑袋,后来就返身进窑去。娘说:“小四!小四!”小四只是不理,在窑里呼呼噜噜地扒饭。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