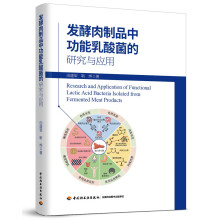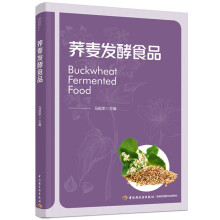第1章导论
1.1家庭食品安全研究背景及意义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热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破解需要立足于全食物链的整体安全。如图1-1所示,全食物链包括四个链条:农产品生产链,食品的加工和制造链,食品的运输、存储和零售链,家庭食物处理链。
图101全食物链示意图
我国传统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主要关注前三个链条,即传统的“供给链”,而对家庭食物处理链缺乏足够的重视。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提供”给消费者的食品是安全的。但是,只有“吃到嘴里”的食品是安全的才有意义。消费者不当的家庭食物处理行为,如存储温度过高、存储期限过长、生熟食品间的交叉污染等,导致很多购买时安全的食品在食用时已经发生了腐败变质,存在潜在的食物中毒风险隐患。因此,对家庭食物处理链的忽视会导致我国在食品供给链监管方面的努力(比如QS准入制度的实施、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开发与应用等)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从而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投入浪费。
实际上,当前家庭环境下的食品安全问题非常突出。一项针对多个国家的调查表明,各国50%~87%的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与家庭食品安全行为直接或间接相关(Griffith and Worsfold,1994)。在欧盟,三分之一(36.4%)的食源性疾病发生在家庭中,由家庭食品操作不当引起;其次(20.6%)是餐馆、咖啡馆、酒吧;再次(5.5%)是学校和幼儿园(EFSA,2011)。美国五分之一的食源性疾病都是由不当的家庭食物处理行为造成的(CDC,2006)。
根据我国卫生部的公报,我国家庭食品安全问题非常严重,连续几年来,发生在家庭中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和死亡人数均是最多的。2010年发生在我国家庭中的食物中毒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当年食物中毒总起数、总中毒人数和总死亡人数的48.18%、17.07%和78.80%;2011年分别占45.50%、30.95%和72.26%;2012年分别占55.2%、2.4%和87.7%;2013年分别占53.3%、28.1%和87.2%。
更为严重的是,贫困的农村家庭成为食源性疾病的第一发生场所。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的监测,2008年该区报告食物中毒事件8起、中毒104人、死亡2人,其中发生在农村家庭的有5起(62.5%)、中毒104人(75.9%)、死亡2人(100%);重庆市卫生厅的监测数据表明,1998~2004年重庆市食物中毒97起、中毒1673人、死亡40人,其中,发生在乡、村、社73起(75.3%),中毒1221人(73.0%),死亡40人(100%)。家庭环境下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使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面临严重威胁,还导致很多农村家庭因就医而返贫,降低了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
家庭食物准备涉及多个环节和众多的消费者行为,任何一项疏忽均会导致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以肉类食物为例,家庭肉类食物准备的全过程包括选购、运输、存储、解冻、准备、烹调、食用、剩菜处理、废弃物处理九个环节,在这九个环节中,消费者的参与多达33项,任何一项出现不当行为,都将引发食品安全问题(Gong et al.,2011)。
但是,由于受传统烹饪习惯的影响及食品安全知识的缺乏,消费者对家庭中的诸多食品安全风险因素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缺乏主动改进的动机,这是家庭食源性疾病不断暴发的根源之一。实际上,在全食物链的四个环节中,基于消费者教育干预模式的家庭食物准备链的安全保障成本是最低的。但是,从政策制定者到相关研究人员,目前关注的重点仍然是传统的食物供给链,而对家庭环境下的食品安全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
由于膳食模式和饮食习惯的不同,各国必须开展本国家庭环境下食品安全风险的评估,这是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与公共管理措施的重要科学根据。因此,开展我国家庭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非常迫切。一方面,作为食物生产和消费大国,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必然是对国际上此类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在我国食物中毒事件在家庭中多发的大背景下,此类研究必将为进一步提升我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食物链安全水平提供重大支持,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国外研究综述
1.家庭食物储存及处理行为研究
家庭食物处理行为主要包括食物储存及处理行为、个人卫生行为、厨房设施购置及维护行为三个方面,其中,食物储存及处理行为是最主要的家庭食品安全行为。家庭食物储存及处理行为的研究以实证为主,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国的食源性疾病时间序列数据,以及通过问卷调查和家庭实地观测采集的样本数据。
消费者家庭食物储存及处理行为中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四大类(Smerdon et al.,2001;Kennedy et al.,2005;Gilbert et al.,2007;Jackson et al.,2007;De Jong et al.,2008;Karabudak et al.,2008;Luber,2009):①交叉污染,尤其是生、熟制品间的交叉污染,以及食物表面与食物内部之间的交叉污染;②储存不当,主要是储存温度和储存期限不当;③不正确的解冻方式,解冻温度过高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风险因素;④烹饪温度和时间不够。Luber(2009)指出,在家庭中食物间交叉污染比食物未被充分加热的危害性更高。Gilbert等(2007)表明,超过40%的家庭使用刀具的方式可能导致交叉污染。GomesNeves等(2007)指出,63%的家庭利用冰箱冷藏食物的方式可能造成食物间的交叉污染。De Jong 等(2008)发现,50%的家庭清洗食物的方式会导致食物间交叉污染。Jackson等(2007)认为,食物是否被充分加热至关重要,提出足够的烹饪温度和时间是保障家庭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Smerdon等(2001)的调查表明,家庭食物中毒的原因中32%是由于储存不当、26%是由于烹调不彻底、25%是由于交叉污染。而且,食物储存及处理行为在不同人群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比如,46.2%的新西兰消费者在室温下解冻生肉(Gilbert et al.,2007),爱尔兰是56%(Kennedy et al.,2005),土耳其则是66.9%(Karabudak et al.,2008)。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人口学特征下的家庭食物操作者的家庭食品安全行为存在广泛差异性,因此,我国家庭食品安全的教育和干预工作必须建立在对高风险目标人群的精准确定,以及对目标人群的家庭食品安全行为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在充分考虑目标人群接受特点的前提下选择合理的干预渠道和干预模式。
2.消费者家庭食品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行为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系统探讨这些影响因素并剖析其作用机理对于揭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行为规律至关重要。目前国外对消费者家庭食品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经济收入、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专业背景、职业等(McCarthy et al.,2007)。但是近两年来,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外的因素,如个性、心理、过去的经验、宗教信仰等对消费者家庭食品安全行为的系统影响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比如,荷兰瓦格宁根大学的Fischer教授等(Fischer and Frewer,2008)构建了包括个性及心理变量的测度各类因素对消费者食品安全行为影响强度的Rasher模型,但是该模型在影响因素交互关系子模型的构建中存在缺陷,对健康动机和风险认知这两大类因素的影响考虑不足(Fischer et al.,2006),而这两类因素对消费者家庭食品安全行为的重要影响已被众多学者所证实。比如,Moorman和Matulich(1993)研究表明,健康动机越强、越关注健康的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意识和遵循度越高,家庭食物处理行为正确率也更高。
此外,更多的研究者引入社会心理学模型对消费者家庭食品安全行为进行分析,以此解析出关键影响因素。Chow和Mullan(2010)比较了扩展健康行动过程方法理论HAPA模型与传统健康行动过程方法理论HAPA模型对消费者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的解释力,结果表明扩展后的健康行动过程方法理论HAPA模型解释力更强,对消费者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和意愿的解释力分别从17%和30%上升为38.3%和54.3%。Shapiro等(2011)利用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对消费者家庭食品处理行为中的洗手及烹饪温度计使用行为进行解析,研究表明,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是家庭食物操作者洗手及烹饪温度计使用行为最强的预测变量,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对洗手及烹饪温度计使用行为的解释力分别为42%和43%。Mullan和Wong(2009)通过加入过去行为这一新变量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扩展,研究表明扩展计划行为理论解释力增强,且过去行为是消费者家庭食品安全行为的关键性影响因素。Mari等(2012)同时使用计划行为理论和含过去行为的扩展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对意大利年轻人和老年人家庭食品安全行为进行解析,结果显示,扩展计划行为理论对消费者家庭食品安全处理行为的解释力明显提升,且年轻人家庭食品安全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意愿和感知行为控制,老年人家庭食品安全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则是过去行为。
因此,非常有必要从人口统计学、个性、心理、经验、健康动机、风险认知、态度、感知行为控制等维度构建更加系统、全面的消费者家庭食品安全行为影响因素集,从而揭示消费者家庭食品安全行为差异化的深层次原因,评价甚至预估各层次、各类型消费者的家庭食品安全行为,为有效干预消费者家庭食品安全行为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3.家庭食品安全风险沟通及干预研究
家庭食品安全风险沟通及干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15年,1998年举行的食品标准和食品安全风险沟通会议上,FAO/WHO联席专家团(Bryan,1992)共同发表声明:“食品安全风险沟通应该强调以受众为本,提供有趣、差异化的信息,而不是向消费者提供一般性、无差异性的‘数据’。因此,‘理想的’有针对性的干预对策应该是一个‘对策集’,根据每一位消费者的具体情况提供不同的干预,这必须基于对消费者食品安全行为特点及规律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消费者家庭食品安全行为干预方法的研究。”该项声明为此类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由于消费者有权以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处理和准备食物,因此家庭食品安全行为的干预措施只能是“建议”性的,而不能是“强制”性的,因此,开展终身化的消费者食品安全行为教育及风险沟通至关重要(Ropkins and Angus,2000)。Nauta等(2008)研究指出,消费者已经具备了家庭食物卫生行为的必要知识,但是如何有效激活这些知识却需要政策制定者研究并予以解决。Kornelis等(2007)表明,不同消费者偏好不同的食品安全信息源,应充分使用各种渠道与消费者进行风险沟通,并对沟通绩效展开评估。
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的食物操作者的家庭食物处理行为的规范性较差,其家庭成员发生食物中毒的风险较高,因此低收入和低受教育程度者应该成为家庭食品安全干预的重点对象(Henley et al.,2012)。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发展中国家建立基于HACCP(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方法的家庭食品安全风险干预(Bryan,1992)。HACCP方法经常被用于食品生产和加工企业的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应用于家庭环境下食品安全风险的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创新。目前,在这个较新的领域中,学者们的研究仍然是以探索性研究为主。比如,Griffith和Worsfold(1994)提出应用HACCP方法改进家庭食物处理行为的5种可能方式。Ropkins和Angus(2000)针对家庭中的化学性危害,构建了基于HACCP方法的风险控制框架。
另外,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干预方案的设计和验证也是近几年新兴的研究方向。比如,Takeuchi等(2005)利用跨理论模型TTM对消费者家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