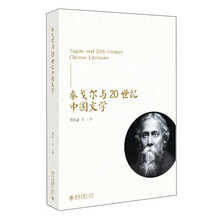把词语划分成适用于高雅文学一类和与这类不同的另一类,这种做法普遍影响了诗的创作,并且它对悲剧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并不比对抒情诗的影响小。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种风气具有难以扼制的力量。当勒布伦( Lebrun)的《熙德》上演时,chambre(卧室)一词就招来一片非难的议论。阿尔弗雷德,德·维尼(Alfred de Vigny)翻译的《奥赛罗》演出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所用的mouchoir(手绢或围巾)这个词不能为一出悲剧所容忍。维克多,雨果开始抛弃了文学创作中对口语化用词与高雅词汇之间的区分。在他之前,圣,波甫也已这样做了,他在《约瑟夫,德洛梅的一生》中曾做过这样的表白:“我曾试图……走出自己的路子,写得朴素,写得平易近人,……我用它们本身的名字来称呼那些生活里固有的事物,但这样做离小棚屋近了而离闺房远了。”波德莱尔把维克多,雨果语言上的雅各宾主义和圣‘波甫的田园式的自由都继承了下来。他的意象由于所指对象的身份低下而显得原汁原味。他关注那些陈腐平庸的事情,极力使它们具有诗意。他写道:“可怕的夜里,那莫名的恐惧挤压着我的心,宛如人们在搓揉一张纸。”这种语言姿态是艺术家波德莱尔的典型特征。但只有在寓言家看来才真正具有意义。这种语态使他的寓言带有某种迷惑的特质,从而使其与通常的寓言区别了开来。勒梅西埃(Lemercier)是近来诗坛与这种寓言同流的最后一人,这样,新古典主义文学便跌落到了最低点。波德莱尔对此置之不理,他大量运用寓言,把它们置于某种语言氛围之中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它们的性质。《恶之花》是第一本在抒情诗里不但使用散文化日常语言而且还使用城市用语的诗作。这部作品直接使用一些作者新创的词语,这些词语不受诗迂腐陈规的约束,以其独创的光彩跃人人们眼帘。他使用quinquet(油灯),wagon(马车)或是omnibus(公交车)这样的词语,遇见bilan(借债单),reverbere(反光镜)和voirie(道路网)这类词也不退缩。由此就创建出了这样一些抒情诗语汇,一些从其中会毫无准备地突然出现某种寓意的语汇。如果说波德莱尔的语言精神能在某处被捕捉到的话,那它们一定是在这种唐突的巧合中被捕获的。克洛代尔(Claudel)对此有一个一语道破的说明。他说:波德莱尔把拉辛的写作风格同一个第二帝国新闻记者的写作风格融为一体了。他的语汇里没有一个词是从一开始就带着某种寓意出现的。这些词是在特定情境里才获得某种寓意的,这些情景来自要去侦察、围攻和占领的主题展开过程中,即看它处于这个过程中的哪一阶段。波德莱尔称写诗为一种奇袭,在这种奇袭里,寓言是他的可靠心腹。它们是极少数参与到机密中去的人。那些la Mort(死神)或le Souvenir(回忆),le Repentir(悔恨)或le Mal(邪恶)出现的地方,就是他的诗战略中心所在。这些词语在诗文中闪电般的出现可由大写字母加以识别,那些诗文对最陈腐平庸的词毫不鄙弃,这一切表明,波德莱尔在幕后操纵着。他的技巧是搞策反暴动人的技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