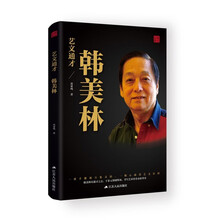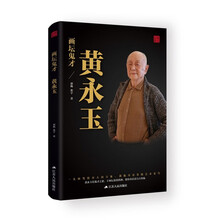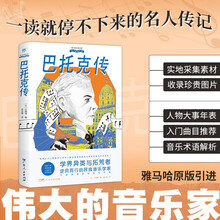《杨明义访谈录/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丛书》:
他的吴侬软语,首先暴露了他的江南人身份。他的第一位太太是苏州人,第二位太太凌子也是苏州人。凌子曾经是电台主持人,讲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却乡音未改,讲的是“苏州普通话”,他就自嘲说,在她而前他不敢讲普通话,怕她笑话。所以得知我来自苏州,听他说话无障碍,普通话也不见得标准,一定是松了口气,也就很放松,很亲切。他的画室宽敞明亮,挂满了画,堆满了纸和笔,却纹丝不乱;他的地下室摆放着多年来收藏的各种雕塑,美观整齐,有强烈的形式感;他的居所如同一幅黑白相间的水墨画,白色的大理石,白色的沙发,白色的墙壁,黑色的家具,黑色的钢琴,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由师友们赠送的珍贵书画,那份书卷气,那份干净整洁,洋溢着的是我熟悉的江南人家淡泊雅致的气息。
访谈时,他坐在我对面,一件或黑或白的T恤,一条洗白的靛蓝色牛仔裤直抵脚背,儒雅而不失潇洒。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地浓密,垂及肩头,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时而蓬松,时而逆立,时而耷拉,有常人所想象的那种艺术家范儿。他额头开阔明亮,双眉浓烈,似卧蚕横亘,柔中有刚。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力量,但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区别,平时又细小又深陷,流露出温和亲切之感,兴奋或愤怒时那亮光在眼眶中旋转、燃烧,奇妙地反映出主人真正的思想和真实的喜怒哀乐。嘴巴富有表现力,上唇常有比下唇前突的倾向,一口坚实洁白的牙齿大多数时候闪耀着,这使得他仿佛一直在微笑中,从而传递出非同一般的感染力;只有在他沉思时,眼神和表情才放松地表现出淡淡的忧郁。
他温和细心,敏感多情,甚至慈悲为怀。1983年,他捐资三千元给自己就读的马医科小学,起因只是看到学校的木楼梯年久失修有了裂缝,生怕孩子们玩耍时不慎伤了腿脚。他收藏了在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时,自己创作的课堂内外的习作、老师上课示范的作品、同学之间互送的作品以及课程表、成绩单,他打算整理出来后,全部送给自己的母校,作为校史资料。他对色彩的那种强烈感受常常令我吃惊,比如,五十多年过去了,他还记得吴?木老师第一次给他们上课时穿着白衬衫,记得小学美术比赛获奖证书的红色纸张,记得初到旧金山接他的是辆蓝色的车……在他的讲述中有关色彩的表达无处不在。在论及那些令自己记忆犹新的往事时,他经常使用的表述语式是“我感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感激得不得了”,“我开心得要死”,“我绝望得要命”……他晚年得一女,小名亦心,年方三岁,活泼可爱赛天使,她穿着红裙子在他宽大的怀里活蹦乱跳撒娇时,他的笑容犹如能容天下的大佛。他给她喂饭、系鞋带,让她在宽大的画桌上乱涂乱抹,给她拍无数精妙绝伦的照片。在他七十一岁的生日聚会上,他告诉我:“我最怕过生日了,一过生日,我就紧张。女儿那么小,我要陪着她长大。”他还说:“每天画画,时间就在一张一张画中流逝掉了。如果我能看到女儿结婚,我就开心了。”面对无法回避的年岁增长和惹人爱怜的女儿,我仿佛能触摸到他时时涌动、共生共长、此起彼伏的焦虑和幸福。
画画,是取之不竭的快乐之源 1943年,他生于苏州邻近观前街的马医科巷一座小楼上。父亲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小业主,开有一家毛笔店,爱好戏剧,复旦大学肄业生。母亲是苏州城里一家杂货店店主的女儿,受过教育,外柔内刚。一开始,人生于他显得衣食无忧、自由自在,没有人强迫他去做什么,没有人指待他日后光宗耀祖,他享受着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学会用毛笔涂鸦去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不像其他小孩子那样喜欢往外跑,玩各种游戏,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画画,对着天井里几块破旧的假山石画,对着花草画,对着斑驳的旧墙画,实在没有可画的了,就画个柜子、凳子。他说:“很多时候,我就像神经病一样的,把我爸爸不知道从哪里弄回来的毛边纸钉在墙上,在上面乱画,画自己想象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小桥,假山,水的倒影,鱼在上面游等等。”他在家门口的马医科小学念书,爱读闲书,爱画画,全班美术课的作业他心甘情愿地一个人承包下来,而且保证交出来的绘画作品没有一张是相同的,他用替同学画画的方式去换同学帮他做数学作业。四年级一次全校比赛——那是他小学期间参加的唯一一次比赛——这个不讨美术老师喜欢的学生拿了第一名。这意外的嘉奖,令他激动万分,“拿到奖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画的画总算得到承认了!”得奖,无疑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绘画兴趣,也让他更有信心,更加“忘乎所以”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不管天热天冷,只要有空,他就出去写生、涂鸦。
擅画,以一种他意识不到的方式帮助他保持了少年时代心理的平衡,建立起了自信,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他说:“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画画,能让我画,我就很开心,不让画就高兴不起来。”他说这话时没有丝毫自我标榜,真诚得如同一个孩童般。他的妻子凌子曾经说:“无论到哪里去,他,只要有一张画桌,其余什么都可以不要的。”画画,是他快乐的源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