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体的声音与有毒旅行
身处环境恶劣的社区的个体有权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这是环境正义话语的重要主题。在第五章中,我介绍了塞娜卡(2004)的三一之声模式,用以描述要让公民之声被听到,或者公民有效参与决策必须具备哪些元素。其中一个元素就是个人的控诉——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法庭上的原告,而是“公民的合法性,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都应该被尊重、赋予尊严和仔细考虑”(p.24)。在这一部分,我描述了当贫困社区或少数族群社区的居民试图在技术论坛上谈及自己的担忧时,部门官员或专家认为他们有失体统或不合时宜,这就是这种尊重、尊严或道德立场面对的障碍。
让“不得体”的声音消失
首先,让我来说明一下我说的不得体的声音(indecorous voice)的含义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一些政府官员将其他人的声音符号化地框架为不合时宜或没有资格,认为其不应该出现在官方论坛上。他们相信普通人在为化学污染或其他环境问题提供证词时可能太情绪化或太愚昧。要让公众没有资格谈论技术问题,方法之一就是让人相信低收入社区的居民违背了知识和客观性的某些规范。罗斯·玛丽·奥古斯汀的故事就是被公共官员无视的典型案例。
罗斯·玛丽·奥古斯汀的故事:“歇斯底里的拉美裔家庭主妇”
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南部,拉丁美洲裔和美国原住民是这里的主要居民。在这里,好几个化工厂的化学物质渗入地下水,这污染了作为47000位居民饮用水源的水井。当地的居民罗斯·玛丽·奥古斯汀描述了她和邻居们的担心:“我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从没有人告诉我们饮用了受污染的水会怎样……我们这里有很多癌症患者。我们想,天啊! 发生什么事情了?”(Augustine,1991)环保署官员后来确认,严重的有毒化学物质泄漏来自附近的图森工厂,这些物质流入井水,使该地被列为国家超级基金优先清理之地(Augustine, 1993)。
在当地被列为超级基金清理点之前,南部的居民曾试图让当地官员听到他们的担忧。奥古斯汀(1993)在报告里说,当官员会见居民时,他们拒绝回应饮用井水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她说当居民坚持询问时,一个县主管告诉他们:“南边的人又肥又懒,饮食习惯又不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水里的有毒化学物质导致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奥古斯汀说:“当我们向一位官员求助时,他称我们为‘歇斯底里的拉美裔家庭主妇’。”
社区公共官员驳回社区居民对环境疾病的抱怨,这种情况还发生在其他案例中。例如,罗伯茨和托弗隆—维斯(Roberts & ToffolonWeiss,2001)报道说,路易斯安那州“癌症小巷”所在地的官员反驳居民的抱怨,说这些由当地污染造成的疾病是由于生活方式或吃高脂肪食物造成的(p.117)。早些时候,海斯(1987)发现,当社区成员向官员们提供身体疾病的证据时,她们的话往往“被贬斥为‘家庭主妇’的抱怨”(p.200)。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这种错误的公共领域概念假设只有理性的或技术的传播模式才是公共论坛唯一允许的话语形式。
公共论坛的礼节和规范
图森官方驳回了罗斯·玛丽·奥古斯汀的投诉,认为奥古斯汀在与政府官员谈话时,违反了规范。最初这显得有些奇怪,因为让我们震惊的是官方对她的无礼。但是,环境正义的倡导者坚持认为,在环境健康和法律责任问题上,贫困和少数族群的居民经常不被认真地对待,因为对于什么是合适的或合理的,这里有隐形的规范。 当他们努力建设一个更包容和更健康的社区时,遭遇的正是这种微妙的障碍。
在很多论坛上,涉及环境问题时,没有说出口的规则以很多方式发挥着作用。这些规则与古代的“得体”原则有类似之处。在经典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修辞手册里,得体(decorum)是一种美德,常常被翻译为合规矩或者适合特定听众和特定场合的。例如,古罗马修辞学者西塞罗(Cicero)写道,明智的演讲者“能以情境要求的方式说话”,或以最“合适的”方式说话。他提出,“让我们称这种品质为得体或‘规矩’” (Cicero,1962,ⅩⅩ.69)。
然而,在贫困社区和少数族群社区的人试着谈及技术问题时,得体这个想法就成为约束他们,甚至是贬低他们的东西。在法制论坛上,判断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的规范往往将普通公众的讲话方式建构为不得体的,因为普通市民说话的方式和知识水平常常达不到卫生与政府部门要求的规范的程度。尽管环境受害社区的成员可能在公众听证会上发言,但他们的地位和尊严会被部门程序和知识规范上非正式的规则和期待贬低。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看看公共官员认为在公众听证会或技术论坛上应该有些什么规范和期待。违背了它们,低收入社区的成员会怎么被视作不得体的。
“证据在我身体里!”:挑战部门规范
在部门发言的规范
由于暴露在化学污染之下,而官员们却予以否认或抵赖,被影响的居民常常感到烦恼、失望和愤怒。讽刺的是,正是与他们互动的部门,那些被政府任命帮助他们远离危机的部门,比如州卫生部门或环保署,激起了居民的这种反应。与这些部门打交道时,个体经常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环境。这里机构管理权限重叠,各种技术论坛充斥其中,在危机评估中关于有毒物质的语言令人不解。这些情境不仅对于低收入社区的居民,就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熟悉的。环境学家迈克尔·埃德尔斯坦(Michael Edelstein,1988)解释说:“这些社区居民感到迷茫。他们缺乏能力理解,也不能直接参与到决定他们生活的重要行动过程中去”(p.118)。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被部门俘虏了。因为他们依赖部门的澄清和救助”(p.118)。
很多机构的官员倾向于将公众参与的框架建构在机构流程和规范的受限制的界限内,这使得他们可以俘虏公众。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见,产业和政府部门的官员经常将环境争论的基础从公众讨论领域转移到技术领域,后者更倾向于“理性的”讨论形式。这也是记者威廉·格雷德(1992)的书《谁将告诉人民?》(Who Will Tell the People?)中的观点。格雷德在书中写道,技术论坛经常假设在关于环境和社区健康的讨论中已经有了合法的依据,以此将底层公众排除在讨论之外。
过去沉重的实践也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机构不愿向受委屈的社区开放技术听证会。通过限制底层目击者的证词,机构得以感知它的决策不会受到“被唤起而又可能很无知的公众”的妨碍(Rosenbaum, 1983, 引自 Lynn, 1987, p.359)。在这种得体的规范下,对一些市民来说,发言意味着面对痛苦的困境。一方面,进入有关毒理学、流行病学或水质的技术层面的讨论,是默认了一种话语疆界,在其中,对家人健康的担忧被看作是私人的或情绪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忧心忡忡的父母在对话中注入这种个人担忧,就是逾越了由技术知识、理性和得体的礼仪构成的强大边界,而这样一来他们的危机根本就不会被听到。
夏洛特·基斯的故事:“证据在我的身体里!”
夏洛特·基斯(Charlotte Keys)就逾越了这个边界。基斯是一名年轻的非洲裔美国女性,生活在密西西比州南部哥伦比亚市(Columbia)的一个小镇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担任塞拉俱乐部主席时,曾与她一起工作过。基斯和她的邻居居住在里奇霍特化工公司(Reichhold Chemical)旗下的一个化工厂附近,早些年这里发生过爆炸并被烧毁。因爆炸和火灾喷出的有毒气体蔓延至整个社区。居民还怀疑工厂遗弃的一些化学物质已经浸入居住地周围的土地,并且污染了哥伦比亚地区的饮用水源。
基斯的很多邻居居住在被废弃的工厂附近,抱怨患上了不寻常的皮疹、头痛和疾病。环保署的官员和哥伦比亚市市长很快驳回了居民的投诉,认为这是未经证实的,也从来没有进行过健康评估。里奇霍特化工公司发言人亚历克·范·莱恩(Alec Van Ryan)后来向当地新闻媒体承认:“我认为自美国环保署以下每一个人都承认,他们最初并没有与社区进行过沟通”(Pender,1993, p.1)。
最终,夏洛特·基斯将邻居组织起来,在公共会议上与当地官员进行对话。有一次会议是与美国联邦有毒物质与疾病登记署(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and Disease Registry, ATSDR)的官员一起开的。当时那些官员正前往哥伦比亚市,并提议进行居民健康研究。会议召开了。但是,官员提出只针对最近接触过有毒物质的居民进行尿液和头发样本的检查。基斯和其他居民表示反对。他们解释说他们与有毒物质的接触早就发生了,从工厂爆炸开始持续到了现在。他们做足了功课,坚持认为对长期的、慢性的暴露于有毒物质的血液和脂肪组织样本进行检查才是恰当的。基斯敦促官员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她说:“证据就在我的身体里!”(C.Keys,个人通信,September 12,1995)
官员们拒绝了这个请求,声称是受到预算的限制。反过来,居民们感觉,他们长期接触化学物质,重要的个人证据显然就在自己身体里,但是他们试图向官员解释时却受挫。会议沦为愤怒的对峙,以无限期延迟健康研究计划结束。
里奇霍特化工公司最终向社区成员提供了帮助,它资助了一项健康研究,还资助了一个社区咨询小组,协助在被污染地区制定决策。
不幸的是,美国联邦有毒物质与疾病登记署和密西西比州哥伦比亚市的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特例。部门官员常常无视那些面对化学物品接触危机的低收入社区的投诉与建议,认为这些人是情绪化、不可靠和不理性的。例如,政治科学家林顿·考德威尔(Lynton Caldwell,1988)早期研究过公众对环保署的环境影响评估的评论,他发现:
政府官员并不认为公众对于问题的投入特别有用……在考虑风险和权衡问题时,公众被认为是所知甚少、头脑简单的……虽然政府官员还是会接受公众参与,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很不情愿的(p.80)。
我也听到过部门官员在听到受害的家庭成员或社区成员报告他们的恐惧时,抱怨说:“这太情绪化了,但是证据呢?”“我已经听过这个故事。”或简单地说:“这无济于事。”
简而言之,把人的言行视为不得体的——情绪化或无知的——就可以无视普通民众的非正式控诉,还可以忽视他们对公共机构或产业的质疑。这里要说清楚一点,我并没有说不得体的声音会导致一个人的修辞无能,或不能找到“正确的词”来表现悲伤。相反,我认为,通过狭隘地定义环境决策中可接受的修辞规范,权力的安排和程序可能破坏修辞性控诉,即对这些群体相应的尊重。
结果就是,贫困社区和少数族群社区的公民经常面对环境社会学家迈克尔·里奇(Michael Reich,1991)所谓的有毒政治(toxic politics)。这就是在话语的边界内无视社区的道德和传播地位,或居民的权利。而影响居民命运的决策正是在这个话语边界内被思考的。有毒政治这个短语不仅指放置或清理化学设施的政治,有时也指这种政治有毒的本质。
面对这样的有毒的政治,许多受害社区开始创造新的传播方式来表达不满,并绕过官方论坛和专家,邀请见证人进入他们的家庭和邻舍,亲眼见证他们这里的环境危害。
有毒旅行:看、听、闻
环境正义组织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传播,其用意是将本地社区与更广泛的公众联系起来。这样的传播形式被草根活动者称为有毒旅行(toxic tours)。传播学者菲德拉·佩佐罗 (Phaedra Pezzullo,2007)著有书籍《污染、旅行和环境正义的有毒旅行修辞》(Toxic Tourism Rhetorics of Pollution, Travel,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在书中她将这种旅行定义为“去被有毒物质污染的区域进行非商业旅行”。这些地区正是罗伯特·D.布拉德(1993)所说的“‘人类牺牲区’……越来越多的社区开始邀请外人进入,将旅游作为教育人们的方式,并寄望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处境”(p.5)。
通常,这些外来者包括记者、环境联盟、宗教组织和其他生活在有环境压力的社区里的人,这些人能更广泛地分享他们的经验。
与环保署或其他部门对有毒场所进行检查不同,有毒旅行强调“污染、社会正义和需要文化变革等话语”(Pezzullo,2007, pp.5—6)。 过去几十年里,环保倡导者曾带记者到优胜美地、大峡谷等地来,希望他们的保护运动能赢得支持,但是开展有毒旅行是近期的事。
亲自参观边境加工厂
几年前,我有机会与佩佐罗博士和其他环境领域的领导者一起来到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布朗斯威尔(Brownsville)南部边境的墨西哥马基拉朵拉(Matamoros),参加了一次有毒旅行。这个区域是马基拉朵拉区域或者说边境加工厂的一部分。这里有大量(基本上不受监管的)的工厂。按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规定,这些工厂从美国搬迁到这个区域。边境加工厂的工人住在附近的安置点(一片拥挤的临时住房)。工人和他的家庭遭受着严重的空气和水污染的危害。许多人患有多种疾病(见第十二章关于边境加工厂无脑儿高生育率的讨论)。
在塞拉俱乐部和墨西哥盟友的组织下,此次旅行穿越了拥挤的安置点,以向环保组织的领导者介绍工人和他们的家庭遭受的污染和不健康的生活环境的威胁。当经过坑坑洼洼的街道路旁的工人家庭时,我们被所见、所闻和被破坏的环境惊呆了。强烈的化学气味弥漫在空气中,在房屋旁污染严重的溪河边,稚童在玩耍,而其他年龄稍大些的孩子们,在燃烧过的大堆垃圾里拨弄,希望找到东西可以卖几个比索。
佩佐罗后来谈到了这次经历,她认为(2004)到这样一个环境被污染的社区去,来访者的视觉、听觉和嗅觉通道都被打开了。这种意识有助于支持社区抗争:“难闻的气味导致居民和来访者眼睛充水,喉咙发紧……提醒人们他们在生理上受到了化工废料的冲击”(p.248)。她和我们分享了一个有毒旅行引导者的观察,即这样的旅游让来访者获得了关于“当地居民受到环境侵害”的“第一手”证据(原来污染源和居民的家这么近),也获得了关于在社区弥漫的有毒气味的“第一手”证据(p.248)(关于路易斯安那州臭名昭著的“癌症小巷”的有毒旅行,参见Pezzullo,2003,2007)。
我的有毒旅行是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经历的,这些有毒旅行主要是邀请记者、机构官员和其他外界人士来参观美国环境受损区域。“为了更好的环境社团”(Communities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cbecal.org)、“路易斯安那州三角洲的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s Delta Chapter in Louisiana)(louisian.sierraclub.org)和“德克萨斯环境正义倡导服务”(Texas Environmental Justice Advocacy Services)(tejasbarriors.org)的活动分子开展了洛杉矶、新奥尔良、休斯敦、奥克兰、丹佛、底特律、波士顿和其他城市的有毒旅行。本土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开展有毒旅行,带州或联邦的官员进入有毒地区,教育官员以当地的条件为基础,或是以一颗人道的心来看待环境伤害。
有毒旅行显示,环境正义运动会继续面对真实的世界和当下的挑战,为往往被排除在正式决策之外的社区发声。事实上,环境正义的愿景并不仅仅是卸下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社区所承担的不成比例的负担。除此之外,环境正义人士坚持运动呈现出“一个新的愿景。它来自社区驱动的过程,其核心是公共话语转型,导向一个真正健康、持久和至关重要的社区”(National Environmental Justice Advisory Council Subcommittee on Waste and Facility Siting, 1996, p.17)。
要培育这样一种转型话语,在制定决策时将受影响的民众和社区民主地包含在内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将在下一个部分看到,全球气候变化给世界各地的社区和人们都带来了新的威胁。这种威胁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看普通民众如何在这个关乎全球事务的地理政治学论坛上有意义地参与其中。因此,气候正义的新运动出现了,它在新的语境中起步,将人们对环境正义的要求和人权勾连起来。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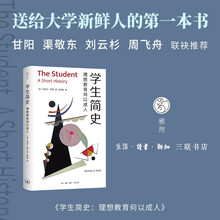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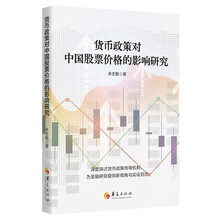

——全国政协委员 王曦
随着人类对自身与环境的关系的认知不断深入,环境传播作为传播学重要的分支领域已经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面对的传播世界,不仅由人类的主体间关系构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联系、对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的认知。本书是一本综合描述环境传播领域的研究与发展的书籍,对于我们理解环境传播这个领域的发展、对于运用环境传播理论与知识理解与环境相关的传播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原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郭镇之
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开展了36年的环境保护工作。从“地球一小时”,到推动长江江豚保护的社会化参与,都离不开及时、理性以及有效的传播。《假如自然不沉默: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一书,从理论到实践,相信都能够为关于环境问题和保护行动的传播,提供卓有成效的借鉴和指引。
——世界自然基金会长江项目高级总监 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