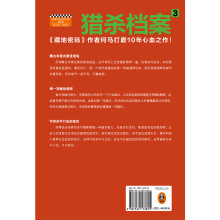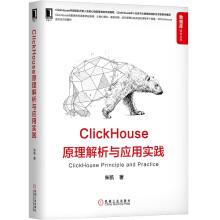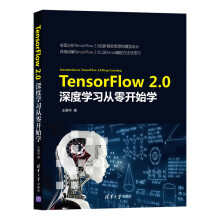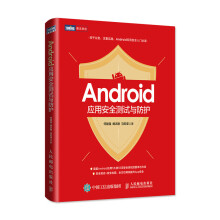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部分年代里,张作霖统治着中国东北,因而在整个中国,他是个比较重要的人物。然而,过去对他的研究一直很少;即便仔细研读了所有已知的能够得到的证据之后,努力再现他的生平和经历,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仍然是一个朦胧的谜一般的人物。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而自力起家的人物,儒教影响对其定形作用很小,这起因于他所出生的家庭、阶级背景和边疆社会三个方面。然而,在其最后的岁月里,他安居于北京的皇宫之中,容许或鼓励围绕着他本人的滋长着的狂热帝王崇拜,而与此同时,他的军队正在溃败,他自己却忙于奉行空洞的仪式。对从西方涌来的现代潮流——科学、民主和民族主义,他确实是个门外汉,而且,他强烈敌视共产主义;但是,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是奉系发言人所时常发表的意见,同时,其经济,特别是其铁路政策被日本人视为对他们地位的一种急剧的威胁。他不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但他是个机灵、顺应性强、野心勃勃、必要时又残酷无情的人。我们很难知道他有什么爱好,因为他与同时代某些其他军阀不同,他自己没有写过什么;已写出的与他有关的那些文章,也很少告诉我们他自身的情况,只是说他有五个妻子,八个儿子和六个女儿,以及他时常抽大烟,爱赌博,特别爱玩麻将,也爱打扑克[1]。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园田一龟于一九二二年所描写的那样,他是“一个身高不到五尺二寸,面黄肌瘦的小个子。和其大名不符,温和的相貌毫无特殊之处。……像一个朴素的农夫”。
然而,他却是最大的军阀,从一九一二年直到一九二八年他死时为止,统治着东北这样一片中国最富庶而广大、在战略上又至关重要的地区,偶尔还控制着大城市和直到长江的中国东部海岸线的大部分。
他做得这样成功可以归因于若干因素:
第一,正是由于东北是一个辽阔、富庶、人口稀少的发展中地区。其财富足以使张的军队成为中国发饷最经常、吃穿装备都是最好的军队;足以使其兵工厂滥用金钱;足以使其空军成为中国最早的空军之一;足以使外国专家和顾问的服务能够容易地获得。
第二,在所有的军阀中,只有张作霖在地理位置上享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对他所选定的向中国中原的任何一次进军来说,在战略上他处于有利的位置,与此同时,实际上,他还难于被南方军队所攻破。这种天然的优越性又被日本政策的作用所加强。
张作霖成功地在东北崛起和执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创建了奉系集团。在其创立并发挥凝聚功效的过程中,对张的个人效忠成为较大的力量;尽管通过它来调节行政比张所表现的一贯个性更为错综复杂。在决定集团政策的过程中,他咨询了所有的东北名流,因此,从整体说来,张的统治,为他们所欣然接受。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军事因素起了主导作用。除却郭松龄这个唯一的例外,在张作霖的整个一生中,高级军官,不论是日俄战争以前时期的老土匪伙伴,还是中国或日本近代各种培训军官的专门院校的毕业生,一直是忠于张的。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保持东北文职精英(尤其是像王永江那类的强而有力的绅士人物)忠诚的能力。他依靠这个本领来管辖和治理他的地盘,征收赋税,并经营有利可图的企业。在这些限制之内,他允许文官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而且,文官势力在该集团议事机构中处于兴盛时期(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文官奖励各种生产企业和开发规划;并倡导进行财政和行政改革,甚至将民族主义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思想观念,注入了被采纳的政策和方案之中。然而,文官势力的利益,虽然与张作霖及东北军方的利益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但毕竟不可避免地从属于他们。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必要的,为的是维护东北的秩序:镇压土匪和抑制社会内部的动荡不安,抵抗外部军队的侵犯——不管是来自国外的还是国内(中国其他地区)的。因此,东北的资产阶级唯一可能的发展,不是作为外国的附庸,特别是以日本控制的地带为基地的日本商行的附庸,就得拍东北军方的马屁。王永江与张作霖的关系,就充分地说明了东北商业绅士的依赖性和软弱性,王永江辞职后,其软弱性更是大为明显。东北三个省的临时省议会,都曾多次坚持军政分离的原则,但这些努力都无成效。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软弱性。
官僚政治的改革、反贪污腐化的努力和行政管理的合理化,都大受军方的鼓励,因为他们希望扩大军事预算,并取得内战的胜利。然而,绅士官吏们都对内战大为不满,因为它破坏了他们的改革,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动荡不安,危害了社会秩序。因此,他们宁肯要军事统治的官僚资本主义的三省或四五省,也不愿要国家的统一,如果只能以那样高的代价才能得来的话。于是,正如我们已经几次提过的,就出现了这样的嘲讽:尽管张与黩武主义者们继续沉迷于统一国家的目标,而王与文官们,虽然口头上附和了这个主张,实际上却逐渐隔断了东北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并要建成一个繁荣、安宁和自治的“满洲”。的确,自一九二二年起,主要的文官们就对民族主义思想、收回权利和反日运动,以及与日本进行经济竞争给予了某些支持,然而,必须把这理解为:这是“达官贵人”对卷入群众运动的敌视(值得注意的是,王永江初露锋芒,正是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他努力保护奉天使其避开革命的时候,支持了张作霖)。从一九二二年起,在王的赞助下诞生的经济民族主义方案,播下了与日本最后发生冲突的种子,但是,当这种冲突来临之时,那些一直参与这个方案的官僚们,却很快就失去了勇气,然后,就显然平静地接受了将东北各省变成一个日本导演的“满洲国”这样的地位变化。
张作霖和他的主要军事顾问们,全神贯注于紧急的战争中,并希望统一国家。但是,与文职官员们相比,按照现代“国家”的含意来看,这必将误入歧途。倒不如把张作霖视为还在坚持旧时代统一中国的传统人物——在一个崩溃和瓦解的时代,在该帝国边缘地区的一个实际上难以攻破的庇护所里, 发展他的兵力。他是一个在另一个时代可能已经登上了皇帝龙座的那种类型的人。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华民国,他是一个过了时的人物。
如果说,张作霖的军队,从财富、战略地位以及创建和维持奉系集团的能力方面说来,既是一台令人可畏的战争机器,又是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广泛认可的统治工具,那么,张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大部分生涯中,其行动背后并不存在清晰可见的政治或思想原则。在其晚年,特别是在一九二五年以后,他成为一个激烈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反共主义者。这背后,有几种理由:这关系到其与俄国接壤的边界安全;他认为,西方列强最期望中国有个反共的统治者,他想借此来迎合西方列强,以便赢得他们的支持;对要推翻他已强行建立起来的秩序的任何运动,他有一个出自本性的憎恶。但是,所有这些考虑,又为下面一点所加强:他发觉必须以某种意识形态来支撑其国家领导权的要求,看来,至少从一九二二年起,他对这种缺陷似乎已经有了一些认识,那年,他实际上委托许兰洲,看看能否编造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参阅第三章)。然而,在其生涯的严酷时期(一九二四年末在天津、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在北京),他似乎又退居僻处,与其最接近的密友一起,沉迷于麻将、鸦片和声色之中,意识形态的刺激,看来并没有对他起很强的作用。连续的中国内战贯穿了他的一生,在内战中,他所结成的同盟的广泛性显示了同样的论断:张是旧时代的人物,尽管他本人并不为近代意识形态的考虑所动心,但他却奋力利用它来推进他的事业。
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弱点,意味着张作霖几乎不能吸引东北地区以外的追随者,对其他地区也只能进行军事统治,而他的第二个弱点,他对日本的错误理解,结果证明,这是致命的。可能完成或已经完成的其他军阀研究,没有对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给予特别的注意。但就张作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回避的问题;而且,这也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当然,张不是日本的傀儡;同时,他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或反帝主义者。他不得不以一种方式或以另一种方式,与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进行竞争,或者以安抚的方式,或者以抵抗的方式。抵抗根本谈不上,除非他能够首先做下面两件事情中的一件:参与群众运动,放宽并普及这样的运动——这是危险的运动,因为它很可能同时危及他自己的独裁统治;成功地解决长期的中国内战,使之有利于他,以便以整个国家的资财为后盾。张作霖拒绝考虑前者,他在战争中的不幸的命运,又使他没有机会去尝试后者。当他建立并巩固其东北权势的时候,他试图首先使日本保持善意的中立,然后,当他奋力将其权势扩展到全国的时候,他则力图赢得日本的确实支持,不论是军事上的、政治上的,还是外交上的。换言之,他企图利用日本;反之,日本也企图利用他;但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竞争中,其结果一点也用不着怀疑。对日本人的支持,张作霖准备给予的回报是太少了。当持续不断地说张作霖是亲日的时候,他对日本实际要求的,承让得越来越少了,而且,在他的赞助下,在逐渐激烈反对日本计划的过程中,东北行政当局采纳了一项发展规划。毫不奇怪,日本对张的支持减少了,而敌视和怀疑却增加了。因此,尽管他位于中国民族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紧张关系的一个焦点上,但他既不能与这个,也不能与另一个友好相处,又不能找到任何可以替代的办法。张作霖试图利用日本来加强他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又防止受日本利用,而成为日本进一步侵入中国的一个工具。在这个限度内,他可能一直是天真的。然而,从其经历看来,他似乎确实坚定地坚持中国的统一与完整,只准备向日本人或东北自治的支持者们,作出最为难于避免的策略上的妥协。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他应当得到比他通常已经得到的更为积极的评价。另一方面,日本的政策虽然摇摆不定,而且,有时显然自相矛盾,但对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可能性却一贯抱有敌意。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原敬内阁所表述的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一直没有变化地贯穿于二十年代相继的政党内阁之中。其根本前提就是,应该不顾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维护日本积累下来的权益,而且,在追求这个目的的过程中,原敬把应当公开宣布的“中立而公正的姿态”,与应该向“亲日分子”暗中提供援助,这两者明确地区别开来。张作霖被看作后者之一,但是,他与段祺瑞不同,按级别他只不过是个地区首领。他的雄心是夺取统治全中国的政权,而整个日本(无论如何,至少是其最高当局)对此却紧蹙眉头;然而,即使是张在推行其最为野心勃勃的计划,也屡次获得了实际驻华的某些日本官员和军官的热情合作。
有限度、有条件地支持张作霖的原则,是一九二四年五月由清浦内阁(参阅前文第四章)再次确认的;一九二四年六月,当币原担任外相的时候,他没有试图重新审查他所继承的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的确,他的不干涉和中立的许诺,宣传得比从前更加热烈而夸张了,然而,必须把这些华丽的言辞,与其政治内容细心地区别开来。一九二四年秋季的危机,暴露了它不过是徒托空言而已。不干涉原则同样是极难执行的,即便不那么公开强调这个原则——不管中国内战的情形如何,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维护日本在东北的权益。这样做就是要维护张作霖的职位。币原虽然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却正是这样做的。当他的部属用了那么多的话,把这点详加解释的时候,他并没有反驳他们。对于应当如何应付形势的种种建议,芳泽在北京主张行贿,船津在奉天城主张武装干涉(参阅前文第四章),币原都默然不语。这表明,他具有一种令人难于取悦于他的愿望,不想让人熟知执行其政策的细节。但在最后,他终于做出了明确的表示,在冯玉祥政变的前夕,他认为阻止吴佩孚向奉天城进军的武装干涉,与“中立”是完全和谐一致的(参阅前文第四章)。在这点上,对华政策的潜在矛盾,由于原敬内阁的宣布而明朗化了。对币原来说,正如对原敬一样,“不干涉”只是外交门面而已,其背后隐藏着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其特权的真正决心,而这些特权是日本靠接连的战争、干涉、威胁从中国获得的。在第二年,即一九二五年,日本向张提供了大量援助,以便抵抗其部下郭松龄反叛的挑战;当此之时,再次显示了币原装腔作势的虚伪性。因此,在日本全部对华政策之中。不论存在着什么分歧和冲突,对东北政策的基本前提,都经久不变。
这一点是颇为重要的。因为一般地说,学者们已经持有相反的观点。例如,马场伸也就否认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有日本的干涉;并且以引文的形式称赞币原的声望,说他是一位“遵奉国际法而调停争端的人”,一位忠实坚持“国际关系的民主和守法原则”的人。关于一九二五年的反叛,艾柯勒?入江昭也坚持说,“与通常接受的观点相反,没有公开援助张作霖反对郭松龄的意图”,赞同这个结论的唯一可能就是:如果拒绝公开援助,就意味着提议暗中给予援助。可是,更成问题的是币原和田中外交的比较。入江昭断定:“事实上,田中坚持了币原的政策,只是由于环境,终于使之变成了不同的政策。”他的论断显然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基本臆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远东,处于“后帝国主义”时期,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就在一九二七年四月田中内阁就职之前,强索一九二四与一九二五年为张作霖而进行干涉的代价的压力正在增加。日本的要求是许多的,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张撤回他对华北的卷入,专心致志地致力于恢复东北的社会秩序——采纳吉田茂所描述的“大东三省”政策(参阅第六章)。日本的外交官、军官以及其他半官方的代表们,已经反复地催促张这样做。这是一九一六年(实际还有一九一一年)经官方批准的那个阴谋的方针,一九二一年的东方会议又再次加以肯定,币原政策没有明说这一点(虽没有明说,但还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吉田和其他人继续照此行动),而一九二七年田中的东方会议,有力地重申了这些要求。日本政府所有文武官员,在这些基本政策方针上全都一致,这是意味深长的。
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紧要关头,积极干涉中国并切断东北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关系,叫喊得最响的不是关东军的激进分子们,而竟然是外务省高级官僚吉田茂,一个被看作世界性国际主义的形象代表。这倒是个惊人的历史性嘲讽。很久以后,吉田被占领军赞誉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未沾染军国主义,在对华和太平洋战争中没有任何罪责,因而当上了日本战后的首相,虽然,正是他提出的那个方针,当军方贯彻实施的时候,直接导致了“满洲国”的建立,导致了侵华战争及其全部后果。
因此,一九二八年六月炸毁张作霖专车的炸弹,有一条长长的引信,不过,在其最后十年,这个引信逐渐而又无情地变短了。一旦张当上了东北的统治者,日本的外交官、官员、军官和商人,就会进行不懈的努力,通过张作霖去确立日本的地位。从张作霖这方面说来,他急于慰抚日本人,以便被他们看作进一步密切与日本的关系,最不知疲倦的支持者,从而获得他们施舍的大量赏钱,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利用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以便在中国实现其目标。结果,双方之间发展起来的密切而频繁的腐败联络,是日本与中国东北之间发展起来的典型的宗主国与半殖民地的关系。大约在一九二五年以前,总的来说,对这种关系,彼此是满意的。但在那以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张的顽固野心的压迫,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焦躁和毫不留情,张则逐渐变得无法妥协了。可以避开冲突的唯一办法,是日方对其在东北的地位、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要求,以及对分离“满洲”的捏造,重新进行一次根本性考虑。然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当权者没有人做过这样的重新考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