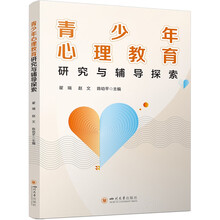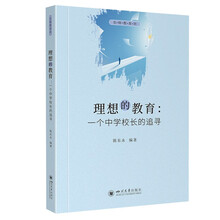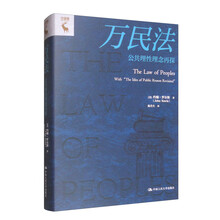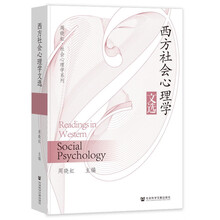正确的理论必定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揭示。在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及其发展机制作理论审视时,习惯性的研究视角通常是以基于西方的“国家一社会”理论或第三部门理论等作为分析工具,但其往往不能透彻地揭示中国这样一个东方社会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逻辑。作者深入研究了传统中国构成其“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历史基因,全面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培育及其发展机理的历史逻辑。作者提出,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政治国家的统治与民间社会的基层治理通常是一种兼容的“吸纳一依附”关系,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逻辑和基因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既深植于社会机体中,又发生着现代的变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高度同构,社会“国家化”倾向相对显著。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自身的发展获得了新的空间,但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仍需要做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要的调整,特别是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政府官员中的腐败和官僚化倾向滋生蔓延等社会问题,导致社会风险剧增。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风险倒逼着中国治理机制的改革,让社会组织有控制地适度发展,以致采取积极培育的措施,正是化解社会风险、调整治理主体关系和治理方式的一项重要的政策突破。
这些研究和解析是作者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及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历史逻辑所作的理论探索和贡献。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兼容,特别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兼容是一种东方文明在社会治理中的智慧。在当今,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组织体系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本意就应当蕴含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形态,公众通过社会组织的渠道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是现代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和发展的基本通道。只有当社会获得了高度发达的组织形态,才可能建立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可以说,没有“社会”就没有社会主义。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