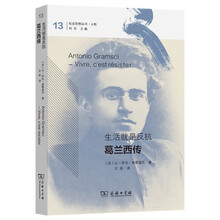对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来说,蒙自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
一九三八年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从暂驻足的衡山湘水迁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因为昆明没有足够的校舍,文、法学院移到蒙自,停留自四至八月。我们住在桂林街王维玉宅。那是一个有内外天井、楼上楼下的云南民宅。一对年轻夫妇住楼上,他们是陈梦家和赵萝蕤。我们住楼下。在楼下的一间小房间里,父亲修订完毕《新理学》,交小印刷店石印成书。
《新理学》是哲学家冯友兰哲学体系的奠基之作。初稿在南岳写成。自序云:“稿成之后,即离南岳赴滇,到蒙自后,又加写《鬼神》一章,第四章第七章亦大修改,其余各章字句亦有修正。值战时,深恐稿或散失。故于正式印行前,先在蒙自石印若干部,分送同好。”此即为最初的《新理学》版本。其扉页有诗云:“印罢衡山所著书,踌躇四顾对南湖。鲁鱼亥豸君休笑,此是当前国难图。”据兄长冯钟辽回忆,父亲写作时,他曾参与抄稿。大概就是《心性》《义理》和《鬼神》这几章。我因年幼,涂鸦未成,只能捣乱,未获准亲近书稿。
《新理学》石印本现仅存一部,为人民大学石峻教授所藏。纸略作黄色,很薄。字迹清晰。这书似乎是该在煤油灯或豆油灯下看的。
蒙自是个可爱的小城。文学院在城外南湖边,原海关旧址。据浦薛凤记:“一进大门,松柏夹道,殊有些清华工字厅一带情景。故学生有戏称昆明如北平,蒙自如海淀者。”父亲每天到办公室,我和弟弟钟越随往。我们先学习一阵(似乎念过《三字经》),就到处闲逛。园中林木幽深,植物品种繁多,都长得极茂盛而热烈,使我们这些北方孩子瞠目结舌。记得有一段路全为蔷薇花遮蔽,大学生坐在花丛里看书,花丛暂时隔开了战火。几个水池子,印象中阴沉可怖,深不可测,总觉得会有妖物从水中钻出。我们私下称之为黑龙潭、白龙潭、黄龙潭——不知现在去看,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联想。
南湖的水颇丰满,柳岸荷堤,可以一观。有时父母亲携我们到湖边散步。那时父亲四十三岁,半部黑髯(胡子不长,故称半部),一袭长衫,飘然而行。父亲于一九三八年自湘赴滇途经镇南关折臂,动作不便,乃留了胡子。他很为自己的胡子长得快而骄傲。当年闻一多先生参加步行团,从长沙一步步走到昆明,也蓄了胡子。闻先生给家人信中说:“此次搬家,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和冯芝生的最美。”
记得那时有些先生的家眷还没有来,母亲常在星期六轮流请大家来用点家常饭。照例是炸酱面,有摊鸡蛋皮、炒豌豆尖等菜肴。以后到昆明也没有吃过那样好的豌豆尖了。记得有一次听见父亲对母亲说,朱先生(自清)警告要来吃饭的朋友,冯家的炸酱面很好吃,可小心不可过量,否则会胀得难受。大家笑了半天。
那时新滇币和中央法币的比值是十比一,旧滇币和新滇币的比值也是十比一,都在流通。用法币计算,一角钱可买鸡蛋一百个,以法币为工资的人不愁没钱用。在抗战八年的艰苦日子里,蒙自数月如激流中一段平静温柔的流水,想起来,总觉得这小城亲切又充满诗意。
当时生活虽较平静,人们未尝少忘战争。而且抗战必胜的信心是坚定的,那是全民族的信心。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学校和当地民众在旧海关旷地举行抗战纪念集会。父亲出席作讲演,强调一年来抗战成绩令人满意,中国坚持持久战是有希望的,一城一地之失,不可悲观,中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又言战争固能破坏,同时也将取得文明之进步,并鼓励学术界提高效率。浦薛凤说这次讲演“语甚精当”。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学生常有流动。有的人一腔热血,要上前线;有的人追求真理,奔赴延安。父亲对此的一贯态度还是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在清华时引用《左传》的那几句话:“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奔赴国难或在校读书都是神圣的职责,可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好。
清华第十级在蒙自毕业,父亲为毕业同学题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第十级诸同学由北平而长沙衡山,由长沙衡山而昆明蒙自,屡经艰苦,其所不能,增益盖已多矣。书孟子语为其毕业纪念。”
一九八八年第十级毕业五十年,要出一纪念刊物。王瑶(第十级学生)教授来请父亲题词,父亲题诗云:“曾赏山茶八度花,犹欣南渡得还家。再题册子一回顾,五十年间浪淘沙!”
如今又是五年过去了,父亲也去世三年有余了。岁月流逝,滚滚不尽。哲人留下的足迹,让人长思。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