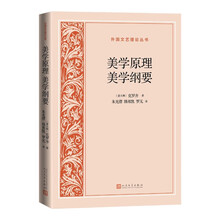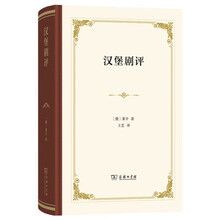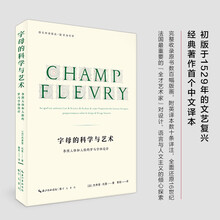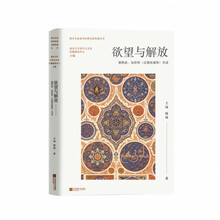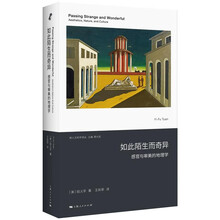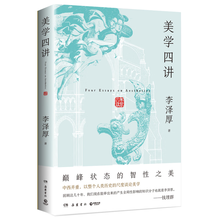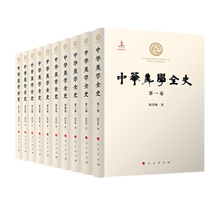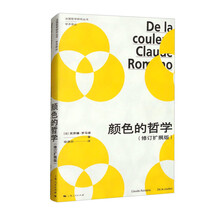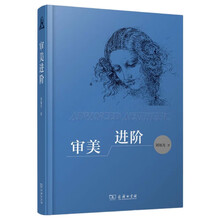《回心与转意:新时期中国美学的复苏(1978—1985)》:
“十七年”时期,真正在学理上与朱光潜、高尔泰等相对的,是蔡仪发展出来的一套所谓“唯物主义”的“新美学”。“新美学”强调美是客观事物的一种属性,是如同“花是红的”一样的一种不以人的主观认识为转移的质素。但是,这套理论实际上暗含了一种类似于柏拉图所言的“美是理念”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倾向,由于这套“美论”确实太为僵硬、保守,将科学取向推向了极端,完全摒弃了作为人文学科的美学应有的价值关怀与人文意趣,所以也没有真正占据历史的中心。尽管美学研究领域没有实现“客观派”的统一,但是对“客观性”的强调仍然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论是蔡仪的教条化固执,还是李泽厚的创造性运用,抑或朱光潜的变通性容纳,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至于文艺理论领域,“十七年”时期更是对属于客观性范畴的“题材”问题有着压倒一切的偏好,而创作主体的经验、技巧等方面的因素几乎不受主流文艺政策的重视。“题材决定论”成为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文艺创作原则。
至此,可以看出现代美学发展过程中的几派主观性美学,或因为思想启蒙立场与工农主体立场相柢牾,或因为世事的茕茕孑立与时代主潮的社会整合相冲突,或因为抽象人性人道本位的伦理追求与革命的阶级论相背离,终究都被崇尚客观性的话语权威所压抑或忽视。“十七年”美学在这种主客观之争中,一步步树立起了美学客观性诉求的优势想象。
3.去传统化与现代赋魅
其实,所谓的“中国美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现代性事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学”都并非华夏传统世界中的所有物。“中国美学”本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在遭遇西方世界整体冲撞下而出现的产物。在这种现代性境况中诞生的中国现代美学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纠结之中,一方面要用现代的语言、思维、精神来重建属于现代中国的美学理论;另一方面传统性的基因又潜伏于自身建构的深处,成为一道无法轻易抹去的幽灵,躲在暗处期待某一复活契机的到来。总体上而言,现代中国美学在这一对因素之间的取舍是张扬现代性而贬抑传统性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