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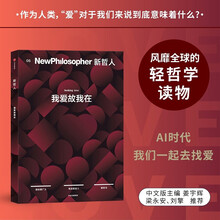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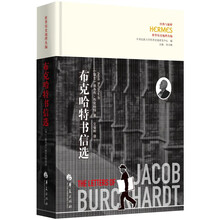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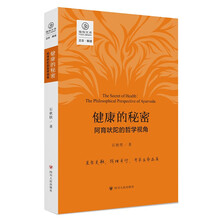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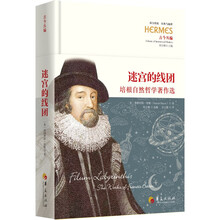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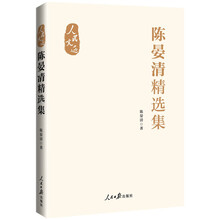
《法国哲学》讲述的笛卡尔哲学,一方面是他高扬主体性的哲学和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另一方面是他的二元论哲学在物理学领域坚持了机械唯物主义,他的唯物主义对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有着重要的启发。他的心身关系学说开启了西方心灵哲学之先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对于主体性问题、认识论问题和西方心灵哲学研究的加强,笛卡尔哲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法国哲学》集刊第yi辑主题为“法国哲学与笛卡尔主义传统”,论文主要来自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法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举办、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法国哲学研究中心承办的2015年中国法国哲学年会的会议报告,涉及的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栏目一:“回到笛卡尔”,包括五篇论文,分别是尚杰的《我x故我在——读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杨大春的《理解笛卡尔心灵哲学的三个维度》、佘碧平的《论笛卡尔的存在概念》、李琍的《以“罪”替“错”——辨析<第yi哲学沉思集>中对错误来源的回答》和刘长安的《笛卡尔“上帝观念”的三种含义及其统一性》。
栏目二:“笛卡尔与法国传统”,含论文五篇,分别是钱捷的《列维纳斯,回到笛卡尔》、施璇的《笛卡尔学说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法国的遭遇》、马迎辉的《梅洛–庞蒂论“沉默的我思”》、王辉的《从福柯的“笛卡尔时刻”到笛卡尔的“作为伦理的方法”——以笛卡尔的<谈谈方法>为例试析两种“方法”》和汤明洁《相共还是表征?——走出“我思”的古典迷局》。
栏目三:“笛卡尔主义与当代思潮”。这五篇文章是:倪梁康的《胡塞尔与法国现象学运动的直接思想因缘——法国哲学家柯瓦雷、海林、勒维纳斯的胡塞尔现象学背景》、张小星的《清楚明晰与可错主义》、胡成恩的《“我思”之“我”何以可能?——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自我”概念》、庞培培的《论梅洛–庞蒂对萨特否定哲学的批评》和李守利的《现代哲学的奠基:先验现象学视域中的笛卡尔》。
笛卡尔学说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法国的遭遇
施璇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在法国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位哲学家能够像笛卡尔那样自17世纪以来始终萦绕在一代又一代法国人的心头,再也没有哪个形容词能够像“笛卡尔的”那样与整个法兰西精神紧密交织在一起,再也没有哪种学说能够像“笛卡尔主义”那样渗透到了数百年来法国各种各样的事件与纷争之中,被研究、被误解、被高扬、被贬斥。
这位日后被誉为法兰西灵魂的哲学家,其学说在法国最初的遭遇却并不那么顺心。笛卡尔于1650年2月11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去世。十多年后,他的学说就遭到了罗马教会的查禁,他的著作被列入了1663年11月20日颁布的《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之中。更糟糕的是,在1671年8月4日,法王路易十四直接降下旨意,命令大学禁止教授笛卡尔的学说,在随后的数年间这道禁令在法国逐渐得到了全面的执行。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阐述笛卡尔的学说在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所遭到的查禁,并一步步挖掘其背后的根源,从一个侧面来阐述笛卡尔的学说与法国的最初的相遇。
一、“圣餐事件”
笛卡尔的学说在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所遭到的查禁是由所谓的“圣餐事件”直接引发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大部分哲学史学者的肯定了。
圣餐礼源于耶稣基督与门徒们的最后一餐,基督将饼与酒分给门徒们,并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在16、17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大量举办圣餐礼,以吸引普通民众。“在宗教战争已经蔓延至大半个欧洲的时候,圣餐礼就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区分点”,因此圣餐变体问题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宗教神学问题。在《第一哲学沉思》一书出版的大约一百多年前的特伦特会议上,罗马教会就圣餐问题已经做出了决议——基督的血肉“实在地并且实体地”存在于圣餐之中。也就是说,在圣餐礼的过程中,圣餐的实体奇迹般地转变为了(托马斯主义的解释)或者被替代为了(司各特主义的解释)基督的血肉,即基督的身体,而饼与酒的偶性(比如颜色、气味、味道等)留存了下来。“圣餐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圣餐事件”最早是源于笛卡尔与阿尔诺(Antoine Arnauld)在《第一哲学沉思》的“反驳与答辩”中所做的关于圣餐的讨论。强调理性与信仰的区分是阿尔诺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在第四组反驳的最后,他提醒笛卡尔注意这一区分。他建议笛卡尔在断言我们应当同意那些为我们清楚分明地把握的东西时,最好补充说明一下这仅仅适用于科学与理智沉思,而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与信仰。因为,他预见到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如今的那些不信神之人会歪曲他的话用以颠覆信仰”。他担忧笛卡尔的哲学,尤其是他的自然哲学,对圣餐的解释恐怕会有悖于神学教义,并由此遭到神学家们的反对。
对于阿尔诺善意的提醒与担忧,笛卡尔在一开始表现出了相当的尊重。他首先明确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否认过实在的偶性之存在”,他辩解说在《第一哲学沉思》中他只是假设自己对它们一无所知,而并没有由此而假定它们不存在。随后,笛卡尔用他的自然哲学对圣餐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在他看来,基督的血肉严格说来并没有存在于圣餐之中,而是“如同圣餐礼那般”存在于圣餐之中,这种存在方式无法用语言来表述,只能通过信仰得到领悟。他坚信他的解释与正统神学的解释没有任何矛盾。
但是,在此之后,笛卡尔突然话锋一转,暴露出了他对“实在的偶性”的真实看法。“实在的偶性”就是能够脱离实体而存在的偶性。在笛卡尔看来,承认这种“实在的偶性”的存在,会引起许多困难,只会带领相信它们的人偏离真理。理由有三点:首先,既然所有的感知都是通过对对象表面的接触,那么就没有必要设定“实在的偶性”来解释感知活动。其次,实体是实在的,而偶性就是非实在的,因此,“实在的偶性”在概念上是矛盾的、不可理解的。最后,“实体的偶性”概念也违反了一条神学公理,即能够用自然理性解释的就不要归于奇迹,而笛卡尔自认为自己的哲学完全能够用理性去解释圣餐变体。
笛卡尔大概是意识到了他在答辩中所做出的对“实在的偶性”的批判与当时的神学教义大相径庭,甚至是争锋相对的,因而这些内容后来并没有出现在《第一哲学沉思》的第一版中。但这并没有平息公众对他关于圣餐的解释所引发的质疑与追问。
之后,耶稣会士梅斯朗(Denis Mesland)要求笛卡尔对此圣餐问题出说明。在1645年2月的回信中,笛卡尔就这一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更为详细与清晰的解释。他主张说,人的身体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物体而被当作为同一个身体就在于它始终与同一个灵魂相统一。而普通的饼与酒被人吃下肚去,只有当它们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换句话说与我们的身体统一在一起,进而与我们的灵魂统一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不再将这些饼与酒的微粒当作饼与酒,而是将它们当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同样的道理,在圣餐礼中,神圣的力量将基督的灵魂与圣餐相统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圣餐当作为基督的身体。笛卡尔觉得自己的解释不但融贯于他整个形而上学,而且比当时正统的神学解释更加站得住脚。
笛卡尔的上述关于圣餐的解释显然没能得到梅斯朗的赞同,因为他在之后的另一封信中要求梅斯朗销毁之前的信件。他说:
你可以随意处理我的信件,但是既然它没有保留的价值,那么请你就直接销毁它吧,不用麻烦你再还给我了。
然而,这些信件并没有按照笛卡尔的意愿而被销毁,而是留存了下了,并在笛卡尔去世后给他的学说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也许是意识到了他自己关于圣餐的新颖观点很难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笛卡尔自此之后,直至其去世,再也没有公开表露过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哪怕在1648年的时候,阿尔诺一再请求笛卡尔能够就这一问题再次做出解释,他也没有直接给出自己的见解,而是回复说自己更愿意当面说明自己的看法,后来索性避而不谈了。
在笛卡尔过世之后,他关于圣餐的解释所引发的关注并没有就此消散,反而逐渐发酵,最终导致了当局对笛卡尔学说的查禁。笛卡尔文稿的第二任继承人及遗嘱执行人克莱尔色列(Claude Clerselier)十分机敏地在出版三卷本的笛卡尔书信集(1657—1667年)时隐去了他在1645年写给梅斯朗的信件。但是,他又不够谨慎地私下将信件的副本给了许多人传阅,其中包括贝尔泰神父(Father Bertet),正是此人随后将这些信件捅给了法布里(Honoré Frabri),一位对新学说充满恶感的耶稣会士。法布里便以这些信件为依据,向罗马方面报告说笛卡尔主张圣餐与基督的灵魂相统一,而这违反了特伦特会议的决议,即基督的身体“实在地与实体地”存在于圣餐之中。经过一番运作,最终法布里连同罗马的红衣主教阿尔比兹一道,促成了1663年的《禁书目录》。这份《禁书目录》有一条十分诡异的补充条件——“直到它们得到更正”(donec corrigantur),既然列入目录之书籍的作者早已过世,因此这份禁令实际上等同于永久禁令。
克莱尔色列的一位朋友维诺(Vinot)将这一系列的变故看得一清二楚。他在1664年的信中写道:
肯定是圣餐事件导致了查禁。你看我多有先见之明,我很早以前就告诉过你,你同贝尔泰神父(就笛卡尔关于圣餐的观点)所做的交流将给笛卡尔的哲学以致命一击。
然而这只是对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轮攻击,更加严重的打击发生在1671年,是由本笃会士戴加贝(Robert Desgabets)的一本匿名小册子所引爆的。这本小册子阐释并发挥了笛卡尔在给梅斯朗的信中所做的关于圣餐的解释。路易十四的耶稣会忏悔师费尔叶(Jean Ferrier)将这本小册子上交给了法王,并告诉他这是一本“异端的并且非常有害的作品”。路易十四随即命令巴黎大学禁止教授任何新的、违背教义的学说,这道禁令虽然没有出现笛卡尔的名字,但是很清楚是指向笛卡尔的学说的。自此之后,路易十四发动了一场长期的战役,禁止大学教授笛卡尔的哲学,并对违反禁令者予以处罚,其目标是将笛卡尔的学说从法国的大学中彻底赶出去。
一言以蔽之,笛卡尔的学说在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所遭到的查禁是由“圣餐事件”直接引发的。但是,这仍旧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笛卡尔的学说遭到查禁呢?当笛卡尔的著作被列入1663年的《禁书目录》的时候,阿尔诺就对此感到非常的惊讶与困惑。在当时的法国,比笛卡尔更加反经院哲学与正统神学、影响更大的哲学家也不是没有。比方说,伽桑狄的接近伊壁鸠鲁原子论的机械主义哲学就远比笛卡尔的哲学更加离经叛道,在当时的法国影响也一点都不比笛卡尔小,但遭到查禁的却是笛卡尔而非伽桑狄。而且,笛卡尔及其后继者们一直在试图隐藏而非散播他关于圣餐问题的看法。因此,考虑到“宣称某种哲学观点与圣餐无法调和是17世纪之初的常见策略”,很有可能的是,笛卡尔关于圣餐的解释只是一个把柄,而非他的学说遭到查禁的根本原因。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笛卡尔的学说会在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遭到了这样程度的打压与迫害呢?
胡塞尔与法国现象学运动的直接思想因缘
——法国哲学家柯瓦雷、海林、勒维纳斯的胡塞尔现象学背景
倪梁康
(中山大学哲学系)
胡塞尔现象学在法国哲学界的影响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末,而后与日俱增,二次大战之后尤甚。至60年代,当德国现象学已经开始撰写自己的历史时,冠以“法国现象学”之名的现象学运动方兴未艾。施皮格伯格在写《现象学运动史》的当时还将法国现象学称之为“现象学运动的法国阶段”,而在世纪交替之后,人们已经可以谈论法国现象学运动的“现象学”与“新现象学”,甚至可以谈论“三个浪潮”或“四个阶段”等等。回顾这个时期的思想史进程,可以看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在当代法国现象学和法国哲学中始终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因而许多问题的展开讨论往往都会回溯到他的思想起点上。但仔细想来,在诸多讨论和发展胡塞尔现象学的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萨特、马塞尔、利科、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中,真正算得上是胡塞尔亲传弟子只有三人:科学哲学家亚历山大·柯瓦雷、宗教哲学家让·海林和伦理哲学家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在他们三人的各自称号前都完全可以加上“现象学的”这个定语。
一、亚历山大·柯瓦雷
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年)出生于南俄罗斯塔甘罗格地区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后来加入法国籍,成为法国哲学家,曾先后担任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埃及福阿德大学(后来的开罗大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以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职与研究员。他早期的研究偏重于宗教哲学和哲学史的论题,例如讨论安瑟伦和笛卡尔的上帝存在观念、波姆的上帝学说等。1930年之后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并在此领域中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柯瓦雷一方面使用了新的科学史研究方法,将科学史作为观念史来描述和分析,在科学史研究中融入了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理念成分,更带有明显的后期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烙印,从而使科学史成为特定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另一方面,柯瓦雷还明确提出“科学革命”的观点,特别强调对科学史上突破性思想事件和变革人物的研究分析。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在胡塞尔的后期哲学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以下简称《危机》)找到其前形态,并且后来都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代表的科学思想史派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柯瓦雷也是第一位对阿拉伯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现代哲学家。
还在1908年,即胡塞尔还在哥廷根执教时,柯瓦雷便开始随胡塞尔以及另一位现象学运动的重要成员阿道夫·莱纳赫(Adolf Reinach)学习现象学,同时也旁听当时在那里执教的希尔伯特(D. Hilbert)、克莱因(F. Ch. Klein)、闵可夫斯基(H. Minkowski)、策梅洛(E. F. F. Zermelo)等一流数学家的课程。柯瓦雷是哥廷根现象学学派的主要成员,与贝尔(W. Bell)、克莱门斯(R. Clemens)、海林(J. Hering)、康拉德(W. Conrad)、诺伊曼(C. Neumann)等师兄弟交往甚密。1911/12年冬季学期结束时,柯瓦雷向胡塞尔提交了两篇较短的数学哲学论文《不可解》(Insolubilia)和《集合论的悖论》作为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胡塞尔仔细地阅读了这两篇文字并做有摘录,但最终并未认可和接受。胡塞尔不认可的原因很可能并不在于对柯瓦雷的研究能力的低估,而是在于对柯瓦雷的论文选题或论文命题的质疑。这对柯瓦雷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在莱纳赫和其他师兄弟的支持下,柯瓦雷在哥廷根还滞留了一段时间。直至1912年夏,柯瓦雷在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情况下,离开哥廷根,回到巴黎,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布伦什维格(Léon Brunschvicg)、拉郎德(André Lalande)等人那里继续学习,并于1913年在索邦获得学士学位。
无论如何,柯瓦雷不失为现象学运动的重要成员。他有两篇文章发表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上。第一篇文章是刊载于1922年第五辑的《关于芝诺悖论的说明》。柯瓦雷将这篇文字题献给他的五年前在一次大战中阵亡的另一位哥廷根老师阿道夫·莱纳赫。但这篇文字并未标明译者的名字。很可能是出自赫德维希·康拉德-马特乌斯之手。第二篇文章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发表在1929年第十辑的增补卷上的“雅克布·波姆的上帝学说”。该增补卷是为胡塞尔七十寿辰出版的纪念文集,由他的学生们的论文组成。柯瓦雷的论文显然是他的巴黎大学博士论文《雅克布·波姆的哲学》(La philosophie de Jacob Boehm)的一部分,由现象学运动的另一重要成员赫德维希·康拉德-马特乌斯译成德文。柯瓦雷在标题上标明该文是未完稿。
这里还需要提到一个源自维基百科的说法:胡塞尔的“巴黎讲演”和随后出版的法文版《笛卡尔式的沉思》影响到柯瓦雷对伽利略在科学史上地位的理解。但这个说法的根据明显不足,因为胡塞尔在“巴黎讲演”和《笛卡尔式的沉思》中均未提到伽利略与相关的科学观念史。这些思想都是胡塞尔在《危机》中才展开论述的。总的看来,这两本后期著作是胡塞尔后期两个不同方向的思考之总结,它们之间虽有实质关联并且都是现象学的引论,但《笛卡尔式的沉思》总体上是沿观念形态与系统方向展开的,而《危机》则是沿观念发生与历史方向展开的。胡塞尔甚至为了后者而推迟并最终放弃了前者的完稿与出版。这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在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Études galiléennes)中并未发现有对胡塞尔的《危机》的引述,也并未发现有对胡塞尔的伽利略理解与诠释的采纳与论证。
胡塞尔本人对伽利略在欧洲科学思想史上的作用与地位评价极高,相当于笛卡尔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他《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首先借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案例来澄清“近代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与超越论的主观主义之间对立的起源”。在他看来,伽利略所起的最大思想作用在于他将自然数学化,亦即把自然视作数学—几何学的宇宙总体。这种想法和做法代表了近代物理主义的自然构想,它是近代欧洲二元论的基础,也是近代欧洲科学危机的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总体上看,对柯瓦雷影响最大的可能不是胡塞尔对思想史上某个人物的解释与评价,而是胡塞尔将科学史理解为哲学史或观念史的做法。关于整个近代科学史的发展及其危机的根源的说明,胡塞尔在《危机》书中仅仅借助了对伽利略和笛卡尔两个人的变革性作用的案例分析。这种科学思想史的写法向前追溯可以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史或观念史的写法中找到其源头,尽管胡塞尔本人对黑格尔的思想风格并不认同,也很难发现黑格尔在胡塞尔那里的思想影响痕迹;而向后寻踪则可以在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史研究中找到其实施和铺展,当然是间接通过柯瓦雷,因为库恩本人对胡塞尔所知甚少。而在柯瓦雷那里,胡塞尔的这个观念史的写作方法所发挥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柯瓦雷自己在给施皮格伯格的信中写道:“我受到胡塞尔的深刻影响,也许,从对于对历史知道得并不多的他那里,我学到了如何正面地接近历史,学到了他对希腊和中世纪思想中的客观主义、对看似是纯粹的概念辩证法的直观内容、对本体论系统的历史构成——和观念构成——的兴趣;我从他那里继承了被他丢弃的柏拉图主义实在论、反心理主义和反相对主义。”
柯瓦雷的讣告撰写者、哈佛大学科学史家约翰·默多克(John E. Murdoch)曾概括地评价说:“在柯瓦雷的著作中,若不是科学史,那就是哲学史,获得了一把基本的钥匙。”而从柯瓦雷以上的说法来看,这把钥匙是他从胡塞尔那里继承而来的。
除此之外,反过来还可以确定一点,即在《危机》影响柯瓦雷的科学史写作之前,“巴黎讲演”与《笛卡尔式的沉思》曾受到过柯瓦雷的研究成果的影响。胡塞尔在“巴黎讲演”和《笛卡尔式的沉思》中对柯瓦雷研究成果的引述说:“我们通过新近的研究,尤其是吉尔松(Gilson)与柯瓦雷的漂亮而深入的研究得知,在笛卡尔的这些沉思中还隐含着多少作为含混成见的经院哲学。”
胡塞尔在这里提到的“柯瓦雷的漂亮而深入的研究”,乃是指柯瓦雷于1922年在巴黎出版的《笛卡尔思想中的神的观念及其存在的明见性》。柯瓦雷一直认为应当将哲学思想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讨论和研究。而胡塞尔——至少是哥廷根时期的胡塞尔——并不能认同这一点。他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实际上将上帝当作“认识论的临界概念”而加以悬隔,排除在现象学的研究课题之外。但在后期的胡塞尔这里已经看出,他对柯瓦雷在此方向上的思考已经抱以理解和赞许的态度。
柯瓦雷的宗教意识研究的情怀表现在他于这本书中所展示的另类笛卡尔中。这是一个不同于通常理解的“明见笛卡尔”的“虔敬笛卡尔”,即沉迷于上帝证明的笛卡尔。它立即引起了胡塞尔的女弟子、同样关注上帝与信仰问题的埃迪·施泰因的注意,并且很快便被她翻译成德文出版(1923年)。这个翻译是她1921/22年滞留于一个位于贝根扎伯纳(Bergzabern)的果园期间完成的。经营这个果园的是她的好友、同样是胡塞尔的女弟子的赫德维希·康拉德-马特乌斯。施泰因的翻译也得到了后者的协助。由于施泰因恰恰是在翻译柯瓦雷的笛卡尔研究的期间完成了她对天主教的皈依(1922年1月),因而这个翻译对她的宗教信仰之转变的可能影响也成为人们思考的课题。我们至少可以赞同这样的说法:这个翻译“为她开辟了一条深化了的通道,从而能够以哲学的方式为信仰与思考提供中介”。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扬·帕托契卡(J. Patočka)在“回忆胡塞尔”一文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所记录的胡塞尔与柯瓦雷的后期交往:“我初见胡塞尔是1929年在巴黎。……这样,我便一同体验了‘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开端,胡塞尔将这些沉思构想和意指为对现象学问题域之总体的系统阐释。……几天之后我在柯瓦雷的‘论文答辩’(soutenance de thése)上重又见到胡塞尔。我至今还看见他在马尔维娜太太和几位熟人的陪同下走下路易-李亚尔(Louis Liard)阶梯礼堂的台阶,以便作为单纯的旁观者来参与他曾经的弟子的凯旋;然而他在下面受到隆重的迎接,并且被请到上面的评审委员的讲台上就座。”
柯瓦雷此次的“论文答辩”论题是关于波姆的研究。随答辩的完成,他成为索邦大学的文学博士(Docteur ès lettres),随后接替了吉尔森的位置。次年(1930年)成为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研究主任(Directeur d’études)以及蒙彼利埃的高级讲师(Maitre de conférences)。胡塞尔在1930年11月7日致柯瓦雷的信中对他的这些成就致以衷心的祝贺:“这的确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目 录
冯 俊 法国哲学的中国视角(代序).....................................................( 1)
回到笛卡尔
尚 杰 我x故我在
——读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 ..........................................( 15)
杨大春 理解笛卡尔心灵哲学的三个维度 ............................................( 31)
佘碧平 论笛卡尔的存在概念 ................................................................( 46)
李 琍 以“罪”替“错”
——辨析《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对错误来源的回答 ...........( 63)
张小星 清楚明晰与可错主义 ................................................................( 88)
刘长安 笛卡尔“上帝观念”的三种含义及其统一性 ......................( 115)
笛卡尔与法国传统
钱 捷 列维纳斯,回到笛卡尔! ......................................................( 133)
施 璇 笛卡尔学说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法国的遭遇 ..........................( 140)
马迎辉 梅洛—庞蒂论“沉默的我思” ..................................................( 161)
王 辉 从福柯的“笛卡尔时刻”到笛卡尔的“作为伦理的方法”
——以笛卡尔的《谈谈方法》为例试析两种“方法” ...... (178)
汤明洁 相共还是表征?
——走出“我思”的古典迷局 ..............................................( 197)
笛卡尔主义与当代思潮
倪梁康 胡塞尔与法国现象学运动的直接思想关联
——法国哲学家柯瓦雷、海林、勒维纳斯的胡塞尔现象学背景 ...................( 213)
胡成恩 “我思”之“我”何以可能?
——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自我”概念 .........................( 229)
庞培培 论梅洛—庞蒂对萨特否定哲学的批评 ....................................( 245)
李守利 现代哲学的奠基:先验现象学视域中的笛卡尔 ..................( 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