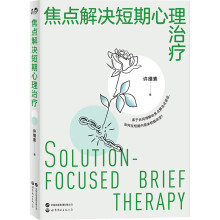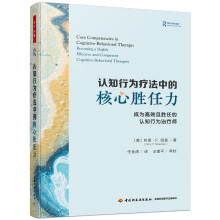《日益亲近:心理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心灵对话》:
今天,金妮来了,她看上去要比往常好一些。她的衣服上没有补丁,头发好像也梳理过了,她的脸看上去清爽真切。她不太自然地谈到我的建议,并说用治疗记录而非金钱来支付治疗费用,简直就是重生,给了她新的希望。她一开始的时候有些兴奋,但后来又通过说些讽刺性的玩笑话,来拿自己和别人开涮,强压住她自己的乐观。当我问及她说了些什么讽刺的玩笑话时,她说我可以出版一本我们的治疗记录,标题可以叫作“与一个能自由走动的紧张症病人的访谈”。为了澄清我们的约定,我向她保证无论我们写了什么,都将为我们两个人所共有,如果要出版,也将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出版。我告诉她想要出版这件事情还不是很成熟,因为我还没有仔细考虑过(谎言,其实有很多幻想掠过我的头脑:有一天,这些材料将会发表,并被公之于众)。
接着我告诫自己要集中在治疗上,以防我们漫无目的地花掉了治疗时间,并陷入金妮那种特征性的漫无目的中。那么她想在治疗中解决些什么问题呢?她希望“到达”哪里呢?她说她现在的生活总的来说很空虚,毫无意义可言;而最紧要的问题是她在性上的困难。我要求她讲得更明确些,于是她描述说每当感觉到就要达到高潮的那一刹那,她从来不能允许自己完全放开。她讲得越多,就越发地让我联想到最近跟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谈话。当她身处性事当中时,却花很多时间想着这件事:想搞清楚是什么原因阻止她达到高潮,是什么因素抑制了她,不能全心地体验与感受。我想我大概可以帮助她消除这种反思,但我脱口而出的,竟是平白得不能再平白的话:“真希望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不再反思”。她让我想到一本童话书里的百足虫,当被要求观察它自己是如何走路的时候,那条百足虫再也不能挪动它那一百双腿,一步都走不了了。
我问她每天的生活是怎样的,金妮便说她的生活是多么空虚,每天早晨从空洞的写作开始,然后一切都变得空洞起来。我和她一起思考着她的写作为何如此空洞,什么东西又能够给她的生活带来意义。越来越像维克多·弗兰克尔了!近来,我的阅读或是跟其他治疗师的谈话越来越多地悄然进入自己的治疗,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条变色龙,根本没有自己的本色。
同样的情况后来又发生了。我评论说她的整个生活似乎都是以自我克制为背景音乐而演绎的。几年前,我正考虑接受一个克莱因派的分析家的分析,他对我说:你的分析将以你对我理论的怀疑为背景音乐来展开和进行。我对金妮说的话以及分析师对我说的话简直如出一辙!金妮继续表现得对生活毫无动力和方向,她的声音细若游丝。她如同被一个巨大的磁铁吸进虚空里去了,她将虚空全盘地吞入,又在我面前吐了出来。人们可能会想她的生活除了空洞外,别无他物了。譬如,她说她给《小姐》(Mademoiselle)杂志寄了几篇小说,接到了编辑充满鼓励的回信。我问她是什么时候接到信的,她说是几天前;我说从她毫无感情的声音听来,好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当她谈到她的好朋友伊芙,或者跟她同居的男朋友卡尔时,她也一样毫无热情。金妮的身上似乎有一个小恶魔,将意义和愉悦从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偷走了。与此同时,她似乎对自己充满洞察力,然后又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来将自己的痛苦浪漫化。我觉得,她会将自己假想成是弗吉尼亚·沃尔芙’,哪一天会在口袋里揣满石头,走进海里。
她对我的期望极其不现实,她对我的理想化,有时让我觉得沮丧,甚至绝望:我无法真实地跟她接触。我担心让她写治疗报告是否是在剥削她。可能我真的在剥削她。我给自己寻找藉口和原因:至少这可以鼓励她去写作,而6个月后,当我们互换记录时,会有一些好的东西产生。如果别无益处,金妮至少可以通过我的文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