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洛杉矶。
我把身份证、银行卡和一张带有指纹扫描资料的通行证,连同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阿迪达斯纯棉短袖,一股脑儿地塞进硕大的运动包里,随手把一本《神经视频通论》也塞了进去。
床头柜上搁着一个假水晶镶嵌的相框。夹在中间的照片已经有些发黄,照片中的女人笑得如同阳光般灿烂,和着郁郁葱葱的背景,让我想起加州午后的阳光——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摇了摇头,伸手把它也丢进了包里,然后拉上了拉链。
窗外,城市的颜色依旧不鲜明,灰暗的色调是我厌恶这座城市的主要原因。天空乌得像一团擦拭不干净的墨团,妖怪一般地笼罩着这座钢筋混凝土的丛林。后大工业时代的城市在人们的脑海中,只是一个能清晰触碰却又无比模糊的影子——没有生气,没有活力,而唯一与这片孤寂不同的是那些在大楼和社区间蛇行穿越的神经网络缆线,在夜晚,会散发出阵阵红色或者天蓝色的荧光。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走到卫生间那面有些裂纹的镜子前,龇着牙笑了笑。那诡异的笑容把我自己也吓了一大跳:眼前这个男人太陌生了,鸟巢一样的头发,干枯无光,杂乱,七七八八地趴在头上;胡子可能有几个月没有刮——我觉得自己像个刚从地铁站台钻出来的落魄艺术家。
我拧开水龙头,准备接水洗把脸再出门。
沉默——并没有一滴水流出来。
该死,没水。我开始觉得那个唠叨的老女人简直就是吃人肉不吐骨头的魔鬼,至少也是个老女巫——每月一百新币的房租,却连水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头一次发生了。
我握紧了拳头,狠命地朝水龙头砸了下去,水还是没有,再砸,水龙头依旧没有来水的意思,我无奈地放弃了。
退出卫生间,我一边拉起夹克,一边伸手去提门边的运动包。出了门,照旧把门反锁上。关门时候发出的声音很大,震落了不少白色的墙灰。隔壁的犹太老头也正好出门,他那双深邃得无底的黑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挤出一丝笑容,逃命似的飞奔下楼,像个傻傻的沙丁鱼罐头伫立在街道中央。
夜晚的街道很萧瑟,天空依旧阴暗一片,像一个黑底的胶片,惨淡的街灯微弱地在这个寒冷冬天的黑暗中尽力撑起一方光幕。一个拉生意的正和一个刚从街道尽头走来、穿着西服的顾客讨价还价;另外几个手臂上有刺青的家伙,正朝一个漆黑的小巷子里走去,我看到,其中一个人用高碳纤维合金钢制成的假肢握着一把锃亮的手枪。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急急忙忙地从公寓里冲下来,难道就仅仅为了站在这里?脑袋像是要爆炸一样,我开始觉得恶心、头晕,周围的景物开始变得模糊。刚才还清晰的拉生意者和那个穿西服的男人,以及提着手枪的金属手臂,此刻都变得混乱起来;灯光下砖墙上有些狰狞的涂鸦,此时都像不断闪烁的光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耗子所说的综合征的具体表现,我只知道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肚子里面翻江倒海,我想吐却吐不出来——幸好中午没有吃什么饭,只吃了半个苹果,喝了一杯过期没几天的牛奶。
“你他妈的就不该去做那个剥离手术。”耗子狠狠地冲着我嚷道,“神经视频剪辑根本就不需要你做这该死的剥离。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没理他。
“笨蛋,你以为你是斯皮尔伯格二世还是希区柯克?剥离后的综合征能痛死你,真不知道该怎么拯救你这个木头。愚蠢。”
耗子是对的。现在我真的感受到这种痛苦了,浑身的每一根神经都好像在发烧,都像是被炙烤着。脑浆在不断地膨胀,一鼓一鼓地痛。
我眼前一片模糊,脚开始发软,而脑海中却突然清晰地出现了一个身影,那身影犹如洪水猛兽一般,径直地出现在我的思维中,让我措手不及。黑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甜蜜的酒窝。对,是她,是她,没错,肯定是她。
现在还在想她吗?有个声音在周围一片幽暗死寂中问我。我没有回答。好像是一瞬间陷入了黑暗中,寒冷和恐惧像潮水一样把我包了个严严实实,我没法逃脱,只能任自己的身体在这片黑色的海洋中越沉越深。
“兄弟,你没事吧?”我努力睁开眼睛,从一片混沌中看到眼前这个男人——那个拉生意的,“你不会是毒瘾发作了吧?我这里可没货。”他很好心地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渐渐地,刚才那股强劲的恶心感逐渐消退,眼前不是那么模糊。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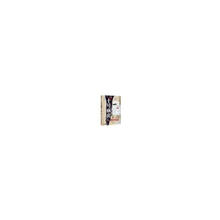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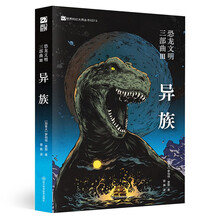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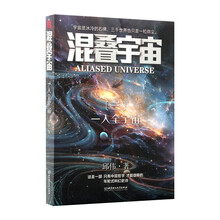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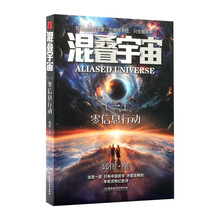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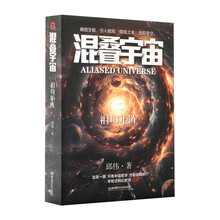


——刘慈欣
★新锐作家们将严谨的科学知识与美妙的奇思妙想融于一体,独具匠心地塑了众多奇特瑰丽的世界。他们的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他们笔下的故事让人如入胜境。“奇点”丛书,守望中国科幻文学的黄金时代。
——王晋康
★虽然有人称他们为“更新代”作家,但我却认为“后新生代”的称谓比较恰当。毕竟,这批作家继承了新生代的多元创作理念,但同时又远远超越新生代的创作范畴。
——吴岩
★这是一批了不起的年轻人写的了不起的科幻。他们真正代表了科幻永远是年轻的这个特征。中国科幻的未来乃至还有中国的未来,就在他们的手中。一旦爱上幻想和科学,这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界了。读了他们写的文字,你会知道,一切都可以飞起来,什么都可以不害怕。
——韩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