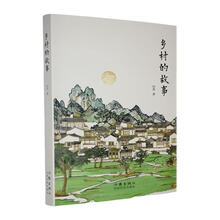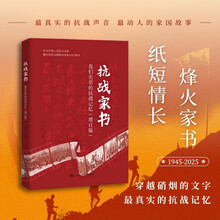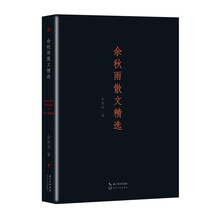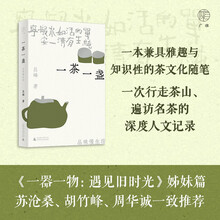在十一月的寒冷雨天,我和作家周泽雄相约在徐家汇港汇恒隆广场茶叙。在二十一世纪华丽气息的购物中心里,一边喝茶一边聊文学历史。他最近写的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文章极具功力,精确而犀利。索尔仁尼琴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其中之一是,与绝大多数作家相反,他的主要作品多半是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因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获奖的。我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它也是“黄皮书”之一,而且是非常罕见的一本,当时在北京有着相当的震撼,大多数人由于这本书才知道了索尔仁尼琴这个名字。
北岛那一代不少人曾经回忆过所谓“黄皮书”“灰皮书”的影响。他们的文学起点乃至思索起点都与之息息相关。每个时代皆有其主流意识和话语,通过各种媒介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大多数人的一生,是在几种主流意识和话语中游移的过程,被刻下所谓时代印记。往往被忽略的,是某一陈述背后的预置前提,是种在骨头里的价值观。怀疑精神并非与生俱来,和成年后近乎逃避的自我边缘化选择一样,都不仅基于理性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验性结果。读书是我少年时最深刻的经验,之所以读书,其实也是偶然。无非是由于那时既无网络、更无游戏,我被摒除在学校门外,渐渐连个小伙伴都没了。关于读书,我毕生感念黎澍先生。在他的家中,有一间大约十五平方米的书房,里面是一排排书架,整整齐齐地摆满几千册今天看来也还是质量很高的书。这个书房的存在,在那时已是极其罕见,而它居然历经劫难始终安然无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黎澍先生是十分爱惜书的藏书家,并不轻易出借,却对我们兄弟几人格外渥待。如果不是从那间书房里找到那么多书,我是不会在十六岁之前就接触到许多西方文学经典的。这些经典为我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虽然我那时能读懂多少,后来又记住了多少,我不很清楚,但也许根本就不必去弄清楚了。我虽然少年时一度有眉毛微微皱起作深沉状,时不时叹口气的毛病,但是心里还是清楚自己并不是爱思想之人,对于前贤能够理解多少,更是从来不敢炫耀的。可以确认记得更清楚的,是《红楼梦》,洁本《金瓶梅》《三言二拍》《十日谈》等等。这也更合乎人性:少年发育期本来就应该荷尔蒙远远高过思想。
我再回到学校时已经十六岁,行为大体正常,偶尔有见到老师脱帽鞠躬、引来全班哄笑的小插曲。心智发育基本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我已经开始单相思。有异于常的是我既不苦恼也毫无少年羞涩,而时不常会口中念念有词,心情激动,有如朝圣般去那位大我两岁的女孩家里。以今日的话语描述,那女孩当时正在知识小资的初期阶段,在一片蓝灰国防绿曲线全无的年代,穿着小花衬衫细腿裤阅读《爱因斯坦回忆录》。我一直感激从她那里借的这本书,其中很多译文当时有醍醐灌顶的感受。比如说,我从此相信怀疑比信仰更使人接近智慧,相信人不必相信宗教却不可没有宗教精神。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