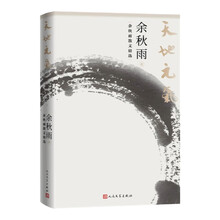围城
生活就像围城一样,我们陷在其中的时候,永远都不知道感恩,一旦失去又开始缅怀。
去年8月一个潮湿闷热的午后,在湾仔香港入境事务处七楼的第二十八号柜台前,一名发髻盘得一丝不苟的中年女子递给我一张表格,缓慢又清晰地问我:“你确定要做香港永久居民吗?这是不可逆的,一旦选择,就没法回头了。”
“不可逆”这个概念让我愣了好一会儿。我从来不擅长做决定,每每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这条路不通,就换一条,反正我什么都没有,唯一拥有的就是时间,仗着年轻而“胜之不武”。
中年妇女看到我愣住,也不开口催促,只是作势要把表格收回去。
她有着香港本地人特有的那种冷漠的面孔,对周遭的任何事物都不关心,也不好奇,思维冷静而简洁。她所有的表情都是制式化的,就像在电脑上输入了“第三号微笑”“第五号皱眉”后出来的结果。
我立刻按住那张纸,并暗暗庆幸自己眼明手快。她不动声色地用手指关节敲敲放在桌上的笔:“快签字吧。”
签完字的我举目四望,狭小的空间里充斥着菲佣、印度人、步履蹒跚的老人、穿鲜艳的劣质衣裙的中年妇女。他们都不懂得在网上预约,所以不得不早晨7点半就过来,排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的队,为了在这个潮湿拥挤烦躁不堪的城市里生活下来,哪怕这个城市并没有善待他们。
有男子拼命说着“借过”从人群中挤出来,一边挤一边冲我挥手。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大学同学志成。他穿着白衬衫黑西装,头发上抹了很多发胶。我对他的印象仍停留在他大学时穿白汗衫、蓝短裤的样子。那时候他在足球队,天天在绿茵场上奔跑,进球之后听着全场的欢呼声回身帅气地挥一挥手,冲天空竖起一根食指,多么意气风发。
“要不要一起吃午饭?”他像大学时那样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拍完之后又有点尴尬,手停在半空不知道该如何安放,最终决定顺势捋一捋头发。
我和他面对面站了一会儿,彼此都在想要说什么话题。他知道我不喜欢缅怀往事,我也知道他不愿意我多问现状。
“周六还要上班?”我指指他身上的西装。
“是啊是啊,要去见一个客户。”他小心翼翼地说。离开校园,他一米八的身形不知为何看起来没有之前那么挺拔,连说话都有点唯唯诺诺的。
“拿了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今后买楼不用交额外印花税,贷款也容易批下来,做了不喜欢的工作大可以炒老板鱿鱼,不用担心工作签证作废。”志成郁郁寡欢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点笑容,大概是因为之后再也不会被称为“外地人”了吧。我当时拼命学粤语,也是这么想的。
“今天要喝一杯庆祝一下。”他很熟练地叫了瓶红酒,什么年份,哪个酒庄,应该搭配牛肉而不是羊肉都能娓娓道来。穿燕尾服的侍者把红酒送到他面前,他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标签,又就着阳光看了一下色泽,然后示意侍者打开。
“大学那会儿,你连打个领带都不会。”我笑道。
他点点头:“可不是嘛!”
大学时,刚到香港的我们就像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写报告,演讲,参加社团,拉赞助,样样都做不来,甚至交论文的时候,面对装订机都束手无策。因为粤语不好,常常闹出把“人妻”说成“淫妻”的笑话,羞愧得连开口讲话都不敢。
那时候的社团流行喊宣传口号,以拍手或者跺脚的方式打节拍,节奏错落有致地把口号齐声喊出来。有些口号特别复杂,喊的时候要一会儿跺左脚,一会儿跺右脚,一会儿原地起跳,一会儿把双手举过头顶。我们要记住粤语发音已经很难,所以总是在该出左脚的时候出了右脚,连累大家重来。本地学生用足够被我们听到的音量咬耳朵:“又是那群NDS,什么都做不好。”
我们一开始也没觉得羞愧,直到有人看我们如此冥顽不化,好心告诉我们NDS是“内地生”的拼音缩写。
香港人做事讲究自由民主,每个社团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像社会的缩影。连竞选小小一个宿舍管理委员会,都要选举,要投票,要连夜开咨询大会,要公开财务年报。
开会的时候一切都有模有样,人们穿西装,打领带,坐下来的时候,男生要解开西装的第一颗纽扣,女生要侧过身子跷起腿。会议的开头主席要致辞,秘书要负责记录,财政委员要汇报收支,哪怕所谓的收支不过是搞活动收到了学校的五百元赞助,买了两箱维他奶和两大包糖果。
志成每次认真做的开会记录都受到各种批评,关于“NDS”的闲言碎语也听了不少,最后干脆穿着系里发的T恤,趿着夹趾拖鞋去开会,从开始睡到结束。系里面的T恤一共有四件,所以志成背后被本地学生戏称为“四件衫”,他听到之后总是大手一挥:“去他妈的形式主义。”
“你现在怎么也开始搞形式主义了?”我问他。
“生活所迫嘛。买件好点的西装,客户就会多信任你一点,请客户喝瓶好酒,他就回赠你一份合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肤浅。”他忍不住解开了领带。因为正午的潮湿闷热,蓝色衬衫的领口部分已经湿了。
“你要脱西装就脱吧,反正大学时你也没少穿着汗衫裤衩给我修电脑。”
“你倒是一直都没变,牙尖嘴利,永远都只做你自己。”志成说道。主菜还没上,他的酒杯已经空了。他绯红的脸色和额头上的汗珠让我觉得他离我心目中大学时代的志成更近了一些。大学最后一个学期的最后一节课下课之后,我们也一起去喝了酒,在学校外面的大排档里,同行的有Maggie和林美丽。我记得我们点的下酒菜是椒盐濑尿虾和辣酒煮花螺,酒足饭饱之后,地上全是虾壳和啤酒罐。那个时候穷,舍不得打车,一行人互相搀扶着,摇摇晃晃地往回走,在月亮下面唱歌,把大学时候的口号再喊一次,结果喊到一半的时候又想不起该出左脚还是右脚。志成躲在墙角里解手,我们就围在他四周替他把风。我们走着走着,走过学校那四条立柱组成的大门的时候,天就突兀地亮了。
那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看过的最后一次日出。
“其实也变了。”我说。“是吗?”他似乎没猜到我会这么回答,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怎么接话我笑笑,喝了一口酒。
我们上学的时候充满理想,谈未来谈社会谈承担,但进入了社会,整天都疲于奔命,半夜筋疲力尽躺在床上,想想却也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等三分熟的安格斯牛排上来之后,志成终于想出了要说什么。他问我:“你还在坚持写作吗?”
“偶尔写一点。”我回答。这里的“偶尔”指的是我上下班在地铁上的一丁点儿时间,如果凑巧有个座位的话,能够写得稍微多些,一天五六百字。我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有的事。所有价值和生命力都被榨干净,我每天都灰头土脸的,即使是对坐在对面的同事,也一句话都不想说。想要对抗现实的枯燥就唯有写小说,在上厕所、冲咖啡、吃午饭的时候看下载到手机里面的电子书,把句子结构都在脑袋里想好,一摸到电脑,就飞快地打出来。有的时候在上下班的地铁上撑不住睡着了,灵感过去,就像流逝的爱情一样,再也捡不回来了。我的电脑里有好多没写完的爱情故事,因为忘了要怎样结尾,都悬而未决。
“那就好。”志成倒像是松了一口气。他缓慢地切着牛排,一字一句地告诉我:“我现在已经不指望还能拍电影了。但还好你还是你自己。”
上大学的时候,志成一门心思想做导演,他去旁听新闻系的课,课程作业是要拍一支歌的MV。
志成要在歌里面拍出秋天的景色,我们所有人都出动帮他捡落叶,用吹风机造出萧瑟的感觉。
Maggie演女主角,她戴了一顶廉价的假发,穿一条薄纱裙子,在秋千上荡啊荡。我们用了好几个小电扇,都没办法做出裙裾飞扬的效果。
我们几个人还常常去参加各种电影节,看文艺电影,看世界的各种滑稽古怪,看世间的人情百态。看完之后常常非常抑郁,恨自己没办法拯救世界,于是聚集在志成宿舍的大厅里聊家国天下,直到他的室友拿着三国杀牌出来问我们玩不玩。
“我一直以为你要么做创作歌手,要么做导演。”志成绝不是那种会按部就班的人,大学里也总是逃我们的主修课,去旁听心理学、翻译学,参加各种奇奇怪怪的研究会,大三那年还想要成立“圆桌诗社”,拉着我陪他在校园的角角落落里面贴海报。
“也要先赚了钱才能追求理想啊,不然房租交不出,水电付不起,人都饿死了,哪里还有资本谈理想。我没好好念书,GPA不高,面试了二十多家公司都失败了,直到在报纸上看到保险公司在招推销员,只要有大学文凭就行,底薪一万元。”
“赚得还好?”我问道。
“还不错。”他点点头,有意无意转动着左手腕上那金灿灿的手表。
我后来听Maggie说,志成的客户大多是有钱人的太太,四十多岁,保养得当,品位、时间都有,最大的问题就是无聊。她们喜欢志成,因为他够高大威猛,浑身都散发着年轻的荷尔蒙,而且动不动就能就音乐啊电影啊侃上好一阵子,她们听得眉开眼笑,纷纷都成了他的客户。
“那他那些电影也没有白看。”我们都替他感到欣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