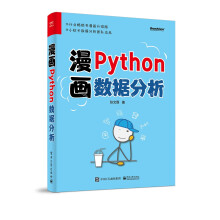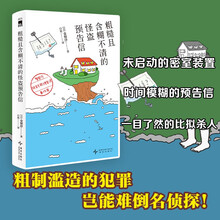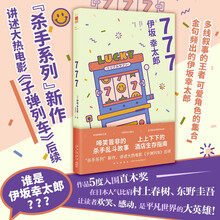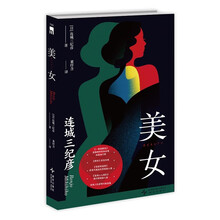《方孝孺事件及其对明代士风的影响》:
(二)治民之道——化成礼义之俗
方孝孺基于恢复三代的礼义之俗的目的,提出了自己对如何治民的看法。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重礼义,轻法律,以化成礼义之俗。法律和道德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方式,相辅而成,不能只取其一。要以道德为本,辅之以法律;没有法律的惩戒,只依靠道德调解,就不能尽天下所有的不公平或纠纷,天下不会大治。所以,必须要依靠法律,但又不能只依靠法律,不依靠道德的谴责功能。因为,只依靠法律,善人也会无所容。并且,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必然浅陋而易知,而人情却深诡难测,必然会有不法分子规避法律,来获得不当利益。所以,法律和道德,二者只取其一,都不能达到致治的效果。
如果朝廷只依靠法律,视杀戮为轻刑而轻易地使用严刑峻法,人们就会轻视法律而不将法律当回事;但如果朝廷将笞骂视为大辱,人们就会以被笞骂为最大的笞辱从而远离犯法。三代圣人之治,不使民畏惧法律,而使民畏惧名或畏乎义。所以,古人被加之以不义的名称,会觉得是天大的耻辱,根本用不着刑罚。因此,三代礼仪之俗就是二者结合的最佳典范,达到了法律和道德相结合的最完美的状态。因为,它做到了使民不愿意犯法,而不是使民因畏惧朝廷之势而远离犯法。
明初的法律并非不严,但是,人们却屡屡犯法。这是就重法而轻德,偏废了一端的缘故。朱元璋政府不研究社会风俗,以为在风俗上用功,效果太微小,不如用法效果快。所以施以猛刑,人民就免不了悖德蔑教;官员也免不了怠肆而污僻。
事实上,变色不言比棰挞诟骂更具有威慑力。法律不需要多严厉,只在乎施法者的意向而已。以和对待恒人不一样的方式去对待要处罚的人,这是最大的惩戒,而标准就是是否有德,方式就是给他们贴上不同形式的标签。廉洁的官吏,和没有道义的官吏,被授予不一样的服装作为各自的象征。以仕途的广狭来作为官员的崇卑标准:有罪的,换掉官服和住房,还不改正,则加以刑戮,这样礼义之俗才有可能化成。方孝孺说:“惟本之以德,而辅之以刑,使恩惠常施于君子,刑罚常严于小人。则宽不至于纵,猛不至于苛,而治道成矣。”①
其次,化成礼义之俗的具体方法。教民以礼、义,使民畏礼、义如刑罚,这就是周代之所以盛的原因。以此为标杆,方孝孺提出了化成礼义之俗的具体方法。
第一,教民礼、义。五家设置一个长者,二十五家设置一胥,百家设置一师,五百家设置一正。其事似乎不切也。岁时则读法,春秋则会社搜狩,考其善而记载,纠其恶而示警戒。看似使人民休息的时间少了,其事也似乎太烦,然而周代恰恰以此而治。商代法严,武王周公申之以礼义,人们俯仰于揖让规矩中而不嫌麻烦,所以,能以至仁易至暴。明初和周代之初的社会情况相似,都是久乱思治。所以,可以通过损益周代之法的方式,来化成礼义之俗。其方法和睦族之法的实质是一样的。十户之民为一睦,以学相亲之道;十睦为一保,教化相助之道;十保为雍,以无争相劝勉。雍隶属于县,雍设一长,以有德而文者胜任。保的长为师,以有行而文者胜任。睦之长为正,以忠信笃厚为十家则者胜任。
同睦之人于月之吉时,都到推选出的睦正家中,睦正于屋中正中坐,余立而侍,老者坐侍。其一,选年幼的一个人读古嘉训,睦正解释其大意,并且戒劝之,全睦之人皆作揖而后认真听。令选一人读邦法,睦正立而宣敷,全体都面朝北跪着听。读毕,睦正签所有到场人的姓名于册,列其所为之善恶于册。无恶者记在最上面,善多者次之,善恶均者为中,恶多者为次中,无善者为下。其二,睦正按照众人行为的善恶而有顺序地跟每个人饮酒。恶者不畀酒,不命坐,经过三年的努力改正不为恶的,告于县而复其身。三年依旧无善行的,严加惩罚,异其服,不齿,改正的可以免除惩罚。关于哪些行为属于善行,方孝孺说:“其善之目日孝、日弟、日亲邻、日恤贫、日助同睦、日敏好学。其恶反是。”
睦之上有保,保设有学,以教十睦之秀民。春夏秋冬每季各举行一次会议,仪式如睦制。教学的内容是孝悌忠信之行,端庄和敏之德,治经知理之术。如果“射而中,习礼乐而安,知书数而适用”,经过几个月就可以升于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