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869年11月22日。那时我父母住在美第奇街,一套位于四层或五层楼的公寓,几年后搬走了,故此我没留下什么记忆。不过,我还记得那个阳台,或者不如说站在阳台上所看见的东西:笔直望过去的广场和广场上水池的喷泉。抑或更确切地说,我还记得我们站在阳台上,把父亲剪的纸龙扔出去,纸龙被风刮着,飘过广场上喷水池上空,一直飞进卢森堡公园,被高高的栗树枝挂住。
我还记得一张相当大的桌子,大概就是餐厅的餐桌吧,所铺的桌布垂得很低。我常常和门房的儿子钻到底下去;门房的儿子是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有时来找我。
“你们在底下搞什么鬼?”保姆喊道。
“没搞什么。我们玩儿。”
我们把玩具摇得蛮响。那些玩具是为了装样子带到桌子底下的。实际上我们另有玩法:不是一个和另一个玩,而是一个贴近另一个玩。我们的所作所为,后来我才知道叫做“不良习惯”。
这种不良习惯,我们两个是谁教给谁的?是谁头一个养成的?我说不清。不过应该承认,这种不良习惯小孩子有时是能够再创造的。我嘛,既无法说是什么人教我的,也无法说自己是怎样发现那快乐的,而是我的记忆力回溯多远,那快乐就已存在了多久。
我深知,讲述这件事以及后来发生的事,对我自己会有所伤害,我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些来诽谤我。但是,我的叙述唯有真实才站得住脚。权当我写这些是一种忏悔吧。
人当童年,心灵应该完全透明,充满情爱,纯洁无瑕。可是,记忆中我童年时代的心灵却阴暗、丑恶、忧郁。
家人常常领我去卢森堡公园,但我不肯与其他孩子一块玩,总是郁郁寡欢地呆在一边,站在保姆身边观看其他孩子做游戏。他们用小桶将沙子堆成一排排漂亮的小沙堆……当保姆扭头看别的东西时,我冷不防冲上去,将所有沙堆踩倒。
我要讲的另一件事更加古怪。大概正因为其古怪,我不那么为之感到羞愧。母亲后来常常对我提起这件事,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事儿发生在于泽斯。我们每年去那里一趟,看望我父亲的母亲和其他几个亲戚,包括佛罗家几个堂兄弟。他们在市中心有一座带花园的老房子。事儿就发生在佛罗家这座房子里。我的堂姐长得很美,也知道自己很美。她一头秀发黑黝黝的,从中间分开,紧贴两鬓,侧影俨然一座玉石浮雕(我后来见过她的照片),皮肤光彩照人。那皮肤的光泽我记忆犹新,因为我被介绍给她那天,她穿着连衣裙,领口开得特别低。
“快去亲亲你堂姐。”一进客厅,母亲就对我说(我当时只有4岁,也许5岁)。我走过去。佛罗堂姐弯下腰,把我拉到她身前,这样她的肩膀就袒露了。看到如此娇艳的肌肤,我顿时头晕目眩,不去亲堂姐伸给我的面颊,却被她美丽动人的肩膀迷住,照准上面狠狠啃了一口。堂姐疼得大叫一声,我则吓得大叫一声。随即厌恶地吐口唾沫。我很快被带开了,在场的人大概都惊得傻了眼,忘了惩罚我。
我找到那时的一张照片,我穿件滑稽可笑的方格罩衫,蜷缩在母亲的裙子里,一副病态、顽皮的样子,目光斜视。
我6岁上我们家搬离了美第奇街。我家的新公寓套房在土尔隆街二号三层,刚好处在圣絮彼斯街拐角。父亲书房的窗子就临这条街,我的卧室窗外是个大院子。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套间的门厅,因为凡是不上学的时候,我通常在门厅里玩儿或是呆在卧室里。妈妈见我总围着她转,烦,就叫我去跟“我的朋友彼埃尔”玩,即叫我独自去玩。门厅的彩色地毯上有大幅的几何图案,在这些图案上与大名鼎鼎的“朋友彼埃尔”玩弹子,再开心不过了。 一个小网兜装着我所拥有的最漂亮的弹子,一颗颗全都是别人送我的,从来不与普通的弹子混在一起。每次拿出来玩,看到它们那样漂亮,总是有一番新鲜的开心感。尤其有一颗小小的玛瑙弹子,上面呈现一条赤道,还有几条白色回归线哩。另一颗光玉髓弹子,呈浅玳瑁色,是我用来压阵之物。此外有一个大布兜,装了许多灰色弹子,常常赢回来,又常常输掉,后来真正有了玩弹子的伙伴时,便拿作赌注。
另一件令我着迷的玩具,是一个叫做万花筒的新奇玩意儿。它像一种小型望远镜,在与眼睛所贴的这一端相反的那一端,呈现出变化无穷的圆形花饰。那是由一些活动的彩色玻璃片构成的,嵌在两块半透明的玻璃之间。这小望远镜的内壁贴着镜子,整个玩具稍微动一下,两块半透明的玻璃之间的彩绘玻璃片,就会匀称地变幻出魔幻般的画面。不断变幻的圆形花饰使我欣喜莫名。现在我仿佛还真切看见那些彩绘玻璃片的颜色和形状,最大的那块是浅色的尖晶石,呈三角形,在自身重量的带动下,在所有彩绘玻璃片上首先转动,挤得其他玻璃片也转动起来。彩绘玻璃片之中有一片是颜色很深的石榴石,几乎呈圆形,一片镰刀形的翡翠,一片我已不记得颜色的黄玉,一片蓝宝石和三小片褐色碎晶体。它们绝不会一齐呈现在画面上,一些完全隐藏、一些半隐藏在滑槽的镜子背后,只有那块尖晶石,因为太大,总是不会彻底隐去。
我的表姐妹们和我一样喜欢这玩意儿,但都缺乏耐心,每回总不停地摇那圆筒,想一下子看到全部变化。我不那样做,而是眼睛总贴在镜头上,慢慢地、慢慢地转动万花筒,欣赏图案慢慢地变化。有时一块玻璃片难以觉察地挪动一下,会造成连续不断的转动。我既好奇又着迷,很快就想迫使这万花筒向我公开它的秘密。我把它的底撬开,将一块块玻璃片卸下来,又从纸板套子里取出三块镜子,然后重新安装上,但多放进去三四颗彩绘玻璃珠子。整个组合其实没有任何高明之处,种种变化再也不会引起惊奇,每个环节都已了如指掌,乐趣的原由已弄得一清二楚。
后来我又想把小玻璃片换成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例如一根羽毛尖,一个苍蝇翅,一段小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透明,没有任何奇妙效果可言。但由于镜子的反射作用和对几何的某种兴趣……总之,我成小时、成天玩这个游戏。我想如今的孩子们都不知道这游戏了,所以花了如许笔墨加以介绍。
童年时代的其他游戏,如拼七巧板、移印花样、搭积木等,都是孤单一人玩的游戏。我没有任何同伴……不,我眼前浮现出一个,但,唉!不是玩的同伴:每次玛丽领我去卢森堡公园,我总在那里见到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他娇嫩、温和、安静,苍白的脸被一对大眼镜遮住一半,眼镜片颜色很深,后面什么也看不清。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也许根本就不知道。我叫他一小绵羊,因为他穿件白色翻羊毛小大衣。
“小绵羊,您为什么戴眼镜?”(记得我不用“你”称呼他。)
“我眼睛有毛病。”
“让我看看。”
他抬起那副可怕的眼镜,两只眼睛可怜地眨巴着,目光犹疑不定,痛苦地透进我的心里。
我俩在一起时不玩儿,记得只是手拉着手,默默地散步,其他什么也不做。
平生头一回结下的这个友谊,持续时间很短。小绵羊不久就不再来了。唉!卢森堡公园这时在我的感觉中那样空荡荡!但我真正开始感到绝望,是在知道小绵羊变成了瞎子的时候。玛丽在小区里遇到那孩子的保姆,回来向母亲学她与那保姆的交谈:为了不让我听见,她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这样一句话:“连嘴巴都找不到啦!”这句话显然荒唐,嘴巴嘛,没有视力无疑也找得到。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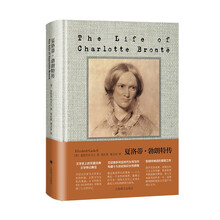


——莫里亚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