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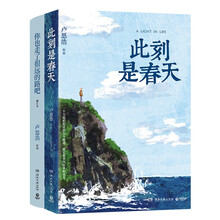








《为众生的悲心》
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这不是一本关于佛理的书。但作者在变幻无常中,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里,仿佛一一经历过佛陀证悟的瞬间。
随着本书,深深地往自己的内心世界瞧去,我们终于在慈悲里得到最深的安静;也在天地和众生面前,了然自己的苦,放下把自己看得太重的负累。
悲心不只是同情心,而是你深切体悟到:那个正在受苦的人,就是你自己。只有悲心,不语而深刻。
这不是一本关于佛理的书。但作者在变幻无常中,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里,仿佛一一经历过佛陀证悟的瞬间。他一下笔,就是苍生,没有一行不是在写生命。让我们明白,原来感动可以不停留在落泪、煽情,更可以无关人间悲喜。他写生命的苦,写众生的多难,写文明的残忍……时时引你思考那些人生中不可不想之事。
随着本书,深深地往自己的内心世界瞧去,我们终于在慈悲里得到最深的安静;也在天地和众生面前,了然自己的苦,放下把自己看得太重的负累。
失去的森林
你大概还记得我那只猴子阿山。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带你上楼看它,它张大着嘴与眼睛凶狠瞪着你的友善。我说你常来,它就会很和气了。
可是我不常回台南,你不常来。
那时我在台中做事。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就读自己喜欢读的书。那时薪水用来吃饭买书后已没有剩钱回家,回家对我竟然是一种奢侈。即使有钱回家,也难得看到为了养活家跑南跑北的父亲与为了点知识背东背西的五个弟妹。即使看到,也难得谈谈。即使谈谈,谈东谈西也谈不出东西来。回家时总还可以看得到的是母亲,因为家事是她的工作;还有阿山,因为跑不了的它总是被关在楼上。但我因太久没回
004
家,它看到我时,张大着嘴与眼睛陌生瞪着我的亲切;摸摸头,好像想些什么,似曾相识,却想不起我这个不常回家的人。即使它还认得我,我也只能和它一起看天,而不能和它聊天。猴子就是猴子,和人之间少了些“组织化的噪音”——语言。这些噪音竟然是很长的文明。它不稀罕文明,但却被关在文明里,被迫看不是猴子的人人人人人人;看人和人争挤,人早认为猴子输了,不愿再和它打架。而且人看久了也没有什么可看的,所以我回家,对它只多了一个没有什么可看的人。在家三四天,我和它又混熟时,就又离家了。我说我走了,它张大着眼睛淡漠看着我这个自言自语的文明。
我离家后,大家都不得不忙些什么,只有母亲愿意告诉我阿山的生活,但母亲不识字。
其实猴子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叙述的。活着不一定平安,平安不一定快乐。而要让猴子在人的世界里快乐不一定是它所愿意的文明。我没问过阿山快乐不快乐,是因为它听不懂这噪音,也是因为我一向不问那个问题。记得从前有人问卡夫卡是不是和某某人一样寂寞,卡夫卡笑了笑说他本人就和卡夫卡一样寂寞。阿山就和阿山一样寂寞;它的世界在森林,但我不知道它的森林在哪里。而我又不能给它森林,我不但没有一棵树,我连种树的地方都没有。
我就知道它在一个不属于它的地方,一条不应属于它的
005
铁链内活着。是我们给它铁链,它戴上后才知道那就是文明。是我们强迫它活着,它活着才知道忍受文明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既自私又残酷,却标榜慈悲,不但关人也关动物。
后来接连有两个冷冷的礼拜,它都静坐一个角落,不理睬任何人。连我母亲拿饭给它吃时,它也没像以前那样兴奋蹦跳,而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吃着。母亲以为天气转冷它不大想动,但猴子突然的斯文反使她感到奇怪了。有一次要给它洗澡抱起它时,才发觉铁链的一段已在它的颈内。兽医把阿山颈内那段铁链拿出来的时候,血,从它颈内喷出,从铁链滴下……
我仿佛又看到它无可奈何的成长。长大不长大对它都一样的,只是老而已;但我们仍强迫它长大。颈上的铁链会生锈却不会长大。它要摆脱那条铁链,但它越挣扎铁链就越磨擦它的颈,颈越磨擦血就越流,血流得越多铁链就越生锈。颈越破越大,生锈铁链的一段就渗进颈内了。日子久了,肉包住了铁。它痛,所以叫;它叫,可是常没有人听到。偶尔有人来看猴子,但看它并不就是关心它。他们偶尔听到它叫,听不懂,就骂:“吃得饱饱的,还叫什么?”后来,它也就不叫了。可是不叫并不表示不痛。它痛,却只好坐在那里忍受。人忍受是为了些什么,它忍受是为了些什么?它忍受,所以它活着;它活着,所以它忍受。
006
如果铁是寂寞,它拔不出来,竟任血肉包住它。用血肉包住一块又硬又锈的寂寞只是越包越痛苦而已。也许那块铁是抗议,但拿不出来的抗议却使它越挣扎越软弱。也许那块铁是希望,那只能使它发脓发炎发呆的希望。
铁是铁不是寂寞不是抗议不是希望,所以拿出来后,它依旧无力和寂寞坐着和抗议坐着和希望坐着。生命对它已不再是原地跳跳跑跑走走的荒谬,而是坐坐坐的无聊。荒谬的不一定无聊,但对于它无聊不过是静的荒谬而已。往上看,是那个怎样变都变不出什么花样的天;就算晚上冒出很多星,夜虽不是它们的铁链,它们也不敢乱跑。老是在那里的它看着老是在那里的天,也就无兴趣叫它了;就是向它鼓掌,天无目也看不见。往下看,是那条吃血后只会生锈的铁链。可是它已不愿再跟圈住它生命的文明玩了。从前它常和铁链玩,因为一伸手就摸到它,如果不和铁链玩,它和什么玩?和铁链玩是和自己玩,和自己玩是欺负自己;后来它连欺负自己的力气都没有了。往前看或往后看对它都是一样的,它看到自己除了黑以外没有什么意义的影子。但那黑不是颜料,它不能用来画图。而就连它这点影子夜也常要夺去。夜逼不了它睡,而它醒并不是它要醒。时间过去,时间又来。时间是它的寂寞,寂寞是它的铁链,这长时与铁链坐着与无聊坐着的文静决不是从前阿山的画像。
007
可是母亲一个朋友很喜欢阿山的文静,一再希望我们把它送给她。可是母亲舍不得这养了七年已成了我们家一部分的阿山,一直都没答应。
可是后来母亲想起我们这六个孩子,女的出嫁了,男的在外当兵在外做事在外读书,从前肯跟阿山在一起玩的都走了,留下也长大了的它看守自己跑不了的影子。家里除了我父母亲外,它看不到一些从前熟悉的面孔。它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知道它在那里,但并不在家,母亲每次看到它,就会想起从前我们这六个孩子和它玩的情趣而更加挂念着不在家的我们。母亲想起我们也忧心着阿山。想起阿山一向很喜欢小孩。想起把它送给那位有好几个还未长大离家的小孩的朋友,也许它可以得到更细心的照顾而会开心点,就把它送给朋友了。
不久,阿山就死了。
可是你一定还记得活着的阿山。你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我带你上楼看它,它张大着的眼睛映着八站台南的阴天和你我的离愁。我说我这次远行,再回家时它一定又不认得我了,我说要是我们常来看它,虽然它还是不会快乐,但就不会那么寂寞了。
——一九七二年
008
芬芳的月亮
从前台南中正路的店面大概“度小月”最寒酸,然而它开着时,担仔面、米粉或粿都是暖香的。
“度小月”就在我家斜对面。那时我没进去吃过,因为已在家吃饱了。反正要品尝,随时都可去。那时自以为忙得不得了,没空坐下来欣赏。年纪虽小,想象的格局可都很大。日子要过就度大月,晚间仰望也要欣赏大的。月娘三十五亿岁,比地球老而美。在地球上,即使不能度大月也要看小月!
然而我们都无法经常度大月。听说从前有个渔夫,大月讨海,小月卖面,就把面担叫“度小月”。讨海要远离家当然比卖面苦,卖面若离家太远就没味道。台湾被割给日本那年就真的天天度小月了。我虽天天经过,都不注意。后来听
009
说那个陶锅长年不洗,就好奇瞟了一眼,看到陶锅上面挂个像圆月的灯笼,被肉臊熏得朦胧,店内恍惚弥漫着苍茫的暮色。我已抑郁,不愿再看见月感伤。但偶尔驻足,看一样的格局坐着不同姿势的人:
汗涔涔吃着的老头像三轮车夫。围在一起有说有笑的猜想是一家人。摆着脸孔吃的中年人俨然小学老师。斯文谈的一对大概正谈恋爱。有女的脸涂得不像画。有年纪和我差不多的,不知干什么,看着碗发呆,不知已吃完还是未吃。
正在吃的,话也随肉臊香味喷出来:
“淡薄就好,胡椒免放太多。”
“头路难找,有就好啦!再艰苦也过一世。”
“喂!你箸拿颠倒反啦!”
“不要乱讲,会被捉去哦!”
“生意已经难做,哪有不漏税的?”
“开饭店惊人吃,不可能啦!”
“少年仔,只看不知影,滋味要试才知啦!”
“今天轮到我请。再争来争去大家就都饿了。”
那夜依依不饿,我第一次进“度小月”,叫一碗米粉汤。看到汤内米粉上,一叶茼蒿,两个虾仁,几根黄芽,几粒肉臊,几点蒜醋。闻着熟悉的味道,我慢慢啜着汤。感到连虾仁都多余,老板却还怂恿加个卤蛋,我摇摇头,不愿那个圆圆的
010
破坏情调。吃下后觉得真不错,却道不出什么味。家乡菜就是好,但描述不出什么味道。小小一碗,给不在家的吃了既不肥也饿不死,几口下去都还要再吃,但若真的继续吃可就没完没了。要饱大概需要四五碗,那就把一天所赚的吃掉了。品尝一碗,反而可回想,想起来又温暖又芬芳。美不一定大,不必圆;又大又圆,太亮就没有想象的空间了,再小也隐约美的。
从“度小月”出来,月,很有味道,跟我回家。我把那个小月装进行李,离开家乡。
——一九九○年
011
一 生
猩猩从西非森林被运来芝加哥动物园,听到狮吼看不到狮子,看人却看了三十七年了,从十一磅天真成长到五百多磅苦闷。苦闷是人间的惩罚。只因他不是人就被独禁,被罚看人。
人从各地来给他看。有人扮各种脸,一直扮到做不出脸还不走开。有人指着鼻子,喃喃絮语努力介绍自己。有人穿西装模仿他的动作,要和他比较文明,笨拙无趣,他忍不住放屁。有人默默看他,似乎和他一样不会说话。有人拿来镜子,他看被铁条隔断的自己,镜子被拿走后,他看见铁条看不见自己。有人照相证明见过他。有人把枪朝他,说些他不懂的英语,被警察捉去。有人把园长带来,边提出问题边做笔记;
012
要报道他却不问他,不知那行业叫什么。有人来笑,他觉得可笑却笑不出来。有人乱抛帽子,他放在脚下踏扁。有人伸入手,他也伸出要握,人却退缩了。有人画了半天,不知把苦闷画成什么颜色。有人投进冰块,他捡起来抱到温暖湿润自己的胸怀。
有人曾经照顾他。小时一伸出手,喂他的女孩就抱他,他摸女孩柔细的脸,摸那绽开的笑纹。他拍掌,然而不管他怎样盼望她来,她长大后也走了。现在看到小孩来,他一伸出手小孩就退后。他喜欢小孩,小孩却爱捉弄他,向他投泡泡糖和石粒。他在小孩的掌声里拾起石粒,看那些小眼珠内无奈的自己,也玩也踢;小孩高兴离开后,他才费力要拿掉泡泡糖。虽然已吹过泡的不再香甜,胶却如苦闷紧黏。一个小孩曾送来猩猩娃娃,他天天抱,抱烦了,撕碎;看破布纷飞,飞不出铁栏,抓住几片玩着。一个小孩曾投入球,球如日子,他接不着,落下了;他拾起来掷,球滚,他随着走;球停,他踢,又跟球转;转晕了,他才坐下,注视那失落的东西。
走不了的是椅子、桌子、轮胎,和他。椅子除了坐以外还可举起来玩弄时间。桌子除了放手,吃饭,支持沉思,拍打以外想不出别的用处。和他同样肤色的轮胎,怎样踢开都被铁栏弹回来,干脆坐在上面。轮胎受不了他苦闷的重量而破了,人仍不拿走。日子重复着铁栏相似的外景,不同的只
013
是肉做的脸。日子重复着铁栏相似的内容,不同的只是铁生的锈。
真没意思。连鸟、蝴蝶、落叶都不飞入,而苍蝇进来只是舔大便。所以阳光下午来时他都枯坐在铁条和自己交错的影子上看天空。风怎样吹都不动,动的人却不动人,他已无兴趣看了。但人跟黄昏走后,又觉得时间和自己一样黑。他默默拥抱黑,黑默默拥抱铁栏,抱到铁栏温暖时也累了。
活着很累,然而不自杀,再受不了也活。七年前完成空气调节的新建筑,给刚从非洲捉来的十多只住。要他搬时,他愤怒撕破两张脸,踢伤一个肚子。他们人多,终于制伏他强迫迁入。没有天空,没有阳光,没有风雨;每天总是一样的空气一样的温度,更加沉闷了。他大叫大跳大撞,最后绝食抗议。已住过三十年的地方虽是铁栏也算老家,家设备再好也是没有树林的牢房。他又回旧牢房后也觉得老了。只背向人坐着,目中无人。人依旧扔进东西,他不再拾起了。泡泡糖依旧黏,他不再拿掉了;黏着痛苦也坐着忍受,因为站起来支撑自己更滞重了。
那天走来几个穿白衣的男女,猛然射来一支箭,他觉得头晕,就躺下睡了。医生量他的体温、脉搏、照X光、抽血。诊断他齿龈有毛病后拔掉一颗臼齿。诊断他缺乏运动而得关节炎,须吃阿司匹林。他天天坐着看天,天落雨时关节更痛了,
014
看着雨落忍受。
听说他生病,三十多年前照顾过他的那女孩从远地赶来看他,给他一束蔷薇。他轻柔抱着蔷薇,看那些绽开的皱纹,他已认不得做祖母的女孩了。
恍惚什么都看不清了。铁栏外,恍惚白云飘浮着,飘浮着,飘浮着,忽然不动了。什么都静止了,什么都暗了。
黎明时饲喂者按时来找他:
“嗨!该醒啦!今天放假,来看你”
……
辑一:万物悲伤的模样
已不稀罕那些关怀,怕人们以眼泪温暖你,因为那很快就变凉。
失去的森林
芬芳的月亮
一生
交响乐
骆驼和山羊
如你在远方
牛墟
画风者
看石头
转弯
访
辑二:珍惜每一声叹息
井边我们最爱听拖车的张阿伯讲古:牛郎织女,山伯英台,无钱打和尚;讲到孙悟空大闹天庭久不久,他却忽然倒了。全巷大人默默流泪,小孩呼呼哭,送葬的行列比巷还长。
想巷
榕树与公路
破鞋
牢
牛津街巷
烦恼
逛书店
跫然想起散步
远方
不要再哀叫,阿山
在春天,我从古城来
包子、水饺和面包
宠物
妨碍交通
温暖的话
辑三:天地间孤独的存在们
谁又敢说自己比一座山、一泓水、一座城、一块石头更孤独呢?
公寓
山
那泓水
土
瀑布与石头
草
亭仔脚
小镇的一角
相思树
家在台南
远近
IV
辑四:人生只在呼吸之间
“这叫笋仔,竹的囝仔,但常给大人掘出,剥皮,一片一片切下,煮熟,吃了。”我听了恐怖,他笑我无胆。
只因把自己比作竹,顺德伯就有升华不起来的固执。
从花园到街路
顺德伯的竹
砚倦
人,行道
长凳的黄昏
冬天的考试
水边
吐
清明
桥
四季内外
房屋在燃烧
祖师庙前的黄昏
暗想
岛鸟
附录:沉默的吐露者
许达然散文的灵魂是涌动着切肤之痛的人文关怀,作家对攀沿于时间之绳上的生命主体的麻木与敏锐、恐惧与冷漠、挣扎于屈从的深刻体察,无疑在揭示灵魂深度的险途上敞开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黄发有
透过他亲切的肺腑,饶富哲理的文字呈现出来的是作者温婉的控诉,生活的敲击,人性的葛藤,我们瞥见尖端工业文明所缔造的畸形繁荣,也看到百层高楼下脆弱的生命,苍白的倒影。
——曹永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