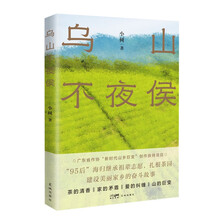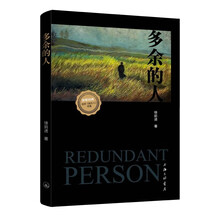首先是我的上司比尔。
比尔在看歌剧时认识了一个上海妹妹。我叫阿三,上海妹妹对比尔说。阿三长得很漂亮,穿着银色的削肩连衣裙,站在大剧院闪着金光的大厅里,很靓,就像一座小型银矿。阿三不属于与人贴脸相吻,或者优雅握手的,因为很显然,她是一个人来的。没有熟人,但阿三并不孤独,有很多人会注视这座小型银矿。而比尔,或许就是打定主意、要对这座银矿进行开发的。
也说不清是比尔先招呼阿三,还是阿三先招呼比尔,反正等我们注意到这边的动向,比尔已经拥着阿三丰腴的左肩,向大剧院门口走去了。临出门前,比尔没忘了向我们招手致意。比尔在法国呆过一段时间,能够把南美洲的艳情与法国的优雅合二为一是比尔的本事。而我,则不失时机地向比尔颔首微笑,也向比尔身边的阿三点头致意。
我觉得自己挺虚伪的,有点自责。
第二天早上,比尔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后面跟着漂亮的上海妹妹阿三。称赞了一下我的着装以后,比尔指着阿三对我说:“这是你新的行政助理。”
我在如释重负之后,又稍稍对比尔感到些失望,这种事情有点像通俗小说里发生的,不是我不理解,没什么不能理解的。但我认为比尔的这种行为有点奇怪。第一,他不够尊重我,为了一个在歌剧院大厅里认识的女孩子,得罪他最得力的下属,这不应该是比尔的做派;第二,我不理解比尔的真实用意,把一首前卫的试验作品融入交响音乐?归根到底,阿三是种杂质,是个不和谐音符。比尔应该思路清楚地把她纳入另一个轨道,一个她应该进入的轨道。而这一点,则是比尔完全能够做到的。
不管怎样,我对阿三还是很客气。我为她安排好办公的区域,并且交待了几件事情,然后便冷眼观察她。
倒不是那种恃宠的女孩子,虽然生于70年代末期,但很乖巧,惊人的成熟。她很会看眼色行事,做事也麻利,并且眼睛很毒。所以说,半小时过后,我几乎断定了昨晚在歌剧院大厅里发生的事情,一定是阿三先招呼比尔的。这座闪亮的小银矿款款而行,上前对比尔说:“你好,我叫阿三。”
当然,这种幻想中的场景,很带有些女性视角的意味。现在,她可再也不是漂亮的上海妹妹阿三了,她现在是“助理阿三”,这称呼带有比较强烈的社会学意义。现在,她已经成了淮海路写字楼里一家公司的一个部分,成了个社会角色,成了这城市对外经济交流中的一个小窗口,成了“助理阿三”的阿三,再也不用像80年前的那个白流苏,找个男人把自己养起来,然后为他“把俏皮话省下来讲给旁的女人听,而把自己当作自家人看待”而欣喜。也犯不上像六七十年前的王琦瑶,用自己的一辈子,换了盒终生没有享用过的金条,临到终了,还死在了那上面,并且“只有鸽子看见了,它们咕咕哝哝叫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