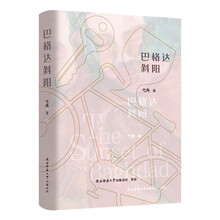那是我二十三岁的时候。
当时,我就读一所美术大学,如今回想起来,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当初为何会报考美术专业。尽管说起来确实算得上有些渊源,因为我父亲是美术教师,我从小也确实是看着他的油画作品长大的,但我从未梦想过自己将来也要成为一名画家。
坦白地讲,当年的这一选择恐怕更多地还是出于经济上的目的,因为只有考进了大学,才能名正言顺地得到家里的大笔汇款。而在此之前,我已经在社会上混了两年,整天出没于美军横田基地周边的声色场所,过着沉溺刺激的放荡生活。在那段日子里,我不仅和比自己年长的有夫之妇姘居。与基地里的美军有所牵扯,还嗑药吸毒,也曾经因此屡屡成为拘留所的常客。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疯狂举动也只是对传统世俗的叛逆宣泄,一番刺激狂热过后,内心却依然迷惘如故。
说起那位比我年长六岁、名叫纪美子的女人。在我认识她时,她就已经是有夫之妇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吉祥寺附近的一家摇滚吧,店里正播放着The Doors(大门乐队)的 Morrison Hotel。当时的我虽然刚满十八岁,但还是十分主动地上前搭讪:“我有grass和nibroll,你要不要试试?”此时,独坐着的纪美子面前已放着一杯我也叫不上名字的鸡尾酒,想必是属于“边车”(Sidecar)或“莫斯科佬”(Moscow Mule)之类的,反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从没喝过、也从没见人喝过的高档饮品,像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平常只会点咖啡或可乐什么的,价格昂贵的鸡尾酒于我们实在是太过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不仅如此,纪美子的发型高雅,衣着端庄,优美的连衣裙下穿着肉色丝袜,脚上是一双真皮高跟鞋。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接触过,甚至是在我周围就从未出现过如此温婉清丽的成熟女性,而我身边那些青涩女生要么是一些头发剃得短短的“假小子”,就算留长发也都是清汤挂面式的,更别说她们的日常着装了,似乎一年四季都只会穿T恤和牛仔裤,或是所谓的波西米亚风,脚上不是赤足趿着凉鞋,就是蹬着人造革马靴。那时还很少有人会穿球鞋(sneaker)出门,甚至连这个词本身都不曾诞生,直到后来“sneaker”的叫法从美国传到了日本以后,人们才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遍地穿起了球鞋。我想,如果最初取的是类似“运动鞋”之类的老土叫法而非如今的纯音译名称,恐怕它的普及率远远不如今日。再回到我们两人的初次见面,主动出击的我在发问中提到的“grass”是“大麻”的行话,“nibroll”则是继Hyminal(海米娜)之后最流行的一种安眠药。纪美子似乎对此一无所知.她只是上下打量着一头长发、身穿黑皮夹克的我,回问了一句: “你刚才说的都是毒品吗?”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