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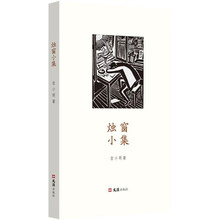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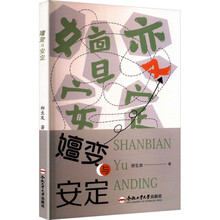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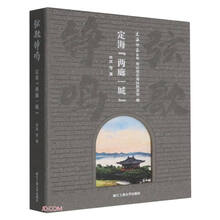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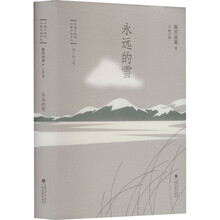
1.“野火”之外,龙应台的“三把火”——与《野火集》一样,本书为龙应台知见录。在台北、新加坡、上海的三次风波事件中,作者直言批评,切中舆论敏感神经,点燃激烈争论。从两性关系、男女平权到政府**与个人自由,龙应台直面问题追索答案,以犀利的书写邀请读者共同拷问。“在一个真正基于民意的民主社会里,敢说话应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人人都有权利敢说话,人人都敢说话。我以敢说话而受到赞美,对这个社会其实是个讽刺。”
2.龙应台执笔,两性问题的理智与情感之书——“当我在谈女人处境的时候,我其实同时在谈男人的处境,因为,如果女人觉得她被双重负担压得透不过气,如果她觉得丢失了性别和自我造成了心灵和情感的残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使她疲惫不堪,力不从心,那么与她共处的男人,下厨也罢,不下厨也罢,怎么可能生活在幸福快乐中呢?”美丽的权利,不过就是个人充分发展的权利。
这是龙应台《野火集》之外的“三把火”。在这三次著名的风波事件中,龙应台就其所见社会即景有感而发,却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强烈的争议与回响。“龙卷风起”,各界人士纷纷加入论战;风过之后,深层的反思却没有息止。
本书分为 “美丽的权利”、“星洲风波”和 “啊,上海男人!”三部分内容,并加上读者投函回应的各种文章和相关文字,集为一册。
【代序】 面对
台北的书店明亮华丽,纸张昂贵、设计精致的书映眼满坑满谷,有点排山倒海的架势。新书上市不到一星期,已经被下一波更新的书淹上来,覆没,不见了。隔天的旧报纸还可以拿去包市场里的咸鱼,书,连被卖掉的机会还没有就已被卸下、遗忘。那被卖掉的书也都是速食品,匆匆吞下,草草抛掉,下一餐速食又来了。
每次跨进那明亮华丽的书店,就难免自疑:我写书,在这20世纪末的时空里,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些文章,我知道,既不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什么太平,也不能教人如何“游山、玩水、看花、钓鱼、探梅、品茗”,享受人生的艺术。但是如果把我当做20世纪末中华文化里的一个小小的典型,这些文字也许在有意无意间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
焦虑,意味着面对问题追索答案而不可得的一种苦闷;苦闷促动书写,书写成为一种邀请,邀请有同样焦虑的读者共同追索。我所面对的问题往往出发自“我是什么”的自觉。
毫无选择地,我是中华文化的儿女。当我站立在耶路撒冷的山丘上,俯视公元前722年以色列国被灭亡的古迹,我必须联想,是的,大约在同一时候,我们的春秋时代开始。当我读欧洲史,知道1850年前后维也纳革命、米兰暴动、俄军镇压匈牙利革命等等,我不得不想起,是的,那时的两广正闹着大饥荒、上海市民攻击传教士、洪秀全正迈向广西桂平金田村……
我生来不是一张白纸;在我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是以这心中的轮廓去面对世界,正确地说,应该是西方世界。怎么叫“面对”呢?面对不言而喻隐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对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而我的中国轮廓上却无时无刻不浮现着西方文化的深深投影,有些地方参差不齐,有些地方格格不入。
我在法兰克福与布拉格、维也纳与斯德哥尔摩之间来来去去,一方面质疑我原有的轮廓,一方面想摆脱那西方投影的笼罩。走到20世纪末,回首看见许多前人焦虑的身影:严复、康有为、胡适之、蒋梦麟……这条路,我们还没走出去。
毫无选择地,我是个台湾人。许多其他社会要花四百年去消化的大变,台湾人民短短四十年里急速地经验,从独裁到民主,从贫穷到富裕,还有因为太过急速而照顾不及的人生品质的鄙劣……我们这一代人因此对时代的变动、历史的推演有身受的敏感。而身为台湾人,所谓时代和历史又脱离不了他必须“面对”的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
我生下来,就不是一张白纸,纸上浮印着中原文化的轮廓。我以这个既有的轮廓去体验自己生长的台湾,逐渐发觉其间参差不齐、格格不入的衔接处。从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对中原文化的一厢情愿,到民主时期对中原文化的反省和对台湾本土的重新认识,以至于对“重新认识台湾”这个过程的戒慎恐惧,我无非在一贯地寻找一条不落意识形态窠臼的新路;我在对抗旧的成见。
毫无选择地,我是个女人。生下来便不是白纸,纸上浮印着千年刻就的男权价值体系。女人是温顺柔和、谦让抑己的,男人是刚强勇敢、积极进取的;男人的成功必须倚赖他身后一个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辅助性的女人。带着这样一个先天印下的轮廓,我开始体验自己的人生,然后大惊失色地发觉:那格格不入之处远远地超过任何东西文化之争、任何大陆台湾之隔!社会,不管东方或西方,对女性的有形和无形的压抑带给我最切身的感受。
于是原来纯属抽象理念之辩的什么自由、人权、公平等等,突然变成和包子馒头一样万分具体的生活实践。我的“命”比苏青、张爱玲要好,生在一个原有价值系统已经相当松动的时代,但是相对地,我对于属于女性的人权、公平的要求也远比前辈高。面对男权社会的巨大投影,我在做我小小的对抗的思索。
最后,毫无选择地,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我自己。我对世界有着超出寻常的好奇;因为好奇,我得以用近乎童稚的原始眼光观照世界的种种,这种眼光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穿透力。我对人和事又怀着极大的热情,热情使我对人世的山浓谷艳爱恋流连。别人的流连也许以华丽的辞藻托出,我却喜欢简单,总想让自己的文字如连根拔起的草,草根上黏沾湿润的泥土。作为我自己,我什么也不想面对,除了那一碧如洗的天空。
至于我必有的偏执与愚钝,那就要读者自己警觉了……
————————————————————————————————————————
【代后记】龙应台这个人(by 胡美丽)
龙应台与我从小一起长大。她逃学的时候,我也背着书包一块儿离家出走。街上逛着无聊,就去偷看电影。两个女生背着书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装是别人的小孩携带入场,只好去爬戏院的后墙。裙子都扯破了,土头土脸地翻身落地,却让守候着的售票员一手拎一个人,扔出门外:两个十岁大的女孩。
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她就是个思想型的人。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半懂不懂地看。放学之后,我把头发卷起来,换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约会,她却只用她纯净的眼睛望着我问:“你跟那些男生谈些什么呢?”我认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欢我。
《野火集》的个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来。龙应台特别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师——他不但口齿不清、思绪紊乱,而且上课时专门重复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课时,我们一般人就乐得打瞌睡、传纸条;下了课跟老师也毕恭毕敬。龙应台却嫉恶如仇似的,一见到这位老师就把头偏开,别说鞠躬招呼了,连正眼也不瞧他。后来基隆有个学生用斧头砍死了一个老师;女中这位地理老师私下问龙应台:
“你是不是也想用斧头砍我?”
龙应台的回答:
“你有这么坏吗?”
1970年,我们又一起进了成功大学外文系。脱离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环境,龙应台似乎渐渐受了胡美丽的影响:她也开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来就少,龙应台长相并不吓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来,又是一副有点“深度”的样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旧迷信“男朋友就是将来要结婚的人”这回事。她当然没有跟当年的男朋友结婚;到现在,她还会问:是谁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女孩子交往要“单一”?差点害死我!
我想我比她聪明……
【代序】 面对
【辑一】 美丽的权利
胡美丽这个女人
小姐什么?
“头衔”是最甜蜜的语言
“头衔”真是最甜蜜的语言吗?
美丽的权利
也谈“招蜂引蝶”
花冢
动心的自由
美丽的偏见
美丽更要安全
管他什么仁义道德
十九岁的迷惑
我不是卫生纸
校园中的歧视
悲怜我的女儿
啊,女儿!
支持严惩强暴犯!
查某人的情书
查某人的心愿
男主外,女主内
让强者自强,弱者自弱
我爱女权主义者
女人该看什么书
我也想去“女人书店”
缠脑的人
丑闻?
女儿,我要你比我更快乐
你是个好母亲吗
一瞑大一寸
遮羞费
台语不是粗鄙的语言
女教授的耳环
男大使的开裆裤
那个有什么不好?
不像个女人
拒做哭泣的“愚女”
女人站起来
美丽兔宝宝
请听听我们的倾诉
小心因果报应
女人是永远的第二性
昭君怨
【辑二】 星洲风波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小叶
还好她不是新加坡人/一得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林义明
如此生活,夫复何求?/雅瑶
吾爱吾土/李珏
还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劲草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龙应台文章引起的五个问题/柯清泉
我们厌恶不负责任的批评/陈敏明
“龙卷风”过后的省思/刘培芳
我们应学习接受批评/蔡再丰
【辑三】 啊,上海男人!
初识
啊,上海男人!
也说“上海男人”/陆寿钧
理解上海男人/吴正
捧不起的“上海男人”/沈善增
说“横扫”/冯如则
乱谈“上海男人”/张亚哲
龙应台与周国平/李泓冰
啊,上海男人!/王战华
为上海男人说句话/杨长荣
龙应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胡妍
我抗议/康议
上海男人,累啊!/唐英
我的不安
上海男人,英国式
举办男孩节,培养男子汉/陈建军
龙应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孙康宜
瑞典来信
日本来信
金钱,使人腐败?
【代后记】 龙应台这个人/胡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