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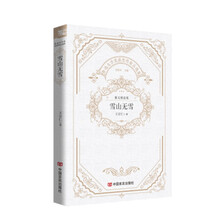




★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传统中有天赋、有原创性和具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
当代文学批评领军人物
★诺顿演讲精华结集
明快流畅、深入浅出的布鲁姆读本
★信仰与文学,经典与焦虑
兼具《西方正典》与《影响的焦虑》双重视角,简笔勾勒西方文学文化史
《神圣真理的毁灭》是哈罗德·布鲁姆在哈佛大学诺顿演讲的精华结集。在基督教与犹太教信仰的大背景下,布鲁姆主要从三个角度评论,即对前人的继承,作家所独有的原创性以及对后人的影响。书中评述了西方文学传统中影响巨大的作家、作品:从希伯来《圣经》写起,到弗洛伊德、贝克特等现代派作家为止,他重读了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布莱克、华兹华斯、卡夫卡等重要作家。同时,他在描绘文学发展的框架中,对信仰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极富启发性的阐释:文学在人性的立场上与神学及宗教抗衡,才能使人的创造力与神的创造力颉颃。
一.
弥尔顿从不会在延伸于真理与意义之间的宇宙真空之中徘徊,他喜欢拥有固若磐石的自我,他相信他是真理的体现,因此他的生活充满意义。对弥尔顿来说,他纯粹正直的心灵所享有的自由就是信仰,他的崇高创作就是诗,他热爱圣经与荷马、维吉尔与但丁、斯宾塞与莎士比亚,又跟他们激烈竞争。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很糟糕的时代,我们的文学研究正在逃离诗歌,转向社会憎恨派的殿堂。因此,弥尔顿对我们弥足珍贵,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西方诗人或随便什么诗人可以与之比肩。弥尔顿的力量并非当下憎恨学派既厌恶却又声称要研究的那些东西,它不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力量,而是修辞的或心理的力量,是诗的力量。弥尔顿的力量是潜能,是包含更多生命的悲情。布莱克、惠特曼和D.H.劳伦斯是英勇的活力论者,弥尔顿的活力论则表现得行云流水,也更加崇高,因此与弥尔顿相比,他们只不过是在东施效颦。他们不得不要按部就班,但这只是再次证明弥尔顿的英勇。
很明显,我的主题是弥尔顿非凡的一元论,他拒绝任何形式的二元论,不管是柏拉图的二元论,还是保罗或笛卡儿的二元论。不过,所谓弥尔顿的一元论只是一种勉强的说法,就好像说弥尔顿的异端性或信仰一样。在斯蒂文斯看来,最大的贫困不是生活在物理世界,是感到人的欲望很难跟绝望区分开来;而按照尼采的说法,隐喻的动机是寻求不同,去到别处,如此说来,弥尔顿没有这样的动机,因为他的欲望从来就不是要寻求不同,从来就不是要去别处。弥尔顿实际的上帝并不是《失乐园》中的那个上帝形象(对上帝的表现是这部作品的一大败笔),就像耶和华文献作者笔下的耶和华不是标准的犹太教、任何形式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中的那个上帝或真主一样,因为无论是弥尔顿还是J都无意运用隐喻。我们最好把约翰?弥尔顿看作是一个神形的存在,一个尘世的上帝,我们的高级浪漫主义先驱就是这样看待他的。《失乐园》中的真正上帝是那个叙述者,而不是在宝座上对诸神灵骂骂咧咧的那个尤里曾式的训导者,也不是阿里乌派的弥尔顿所召唤来的圣灵,而且这个圣灵在弥尔顿那里并非三位一体的一部分,也不是他的缪斯,因为弥尔顿的缪斯仅仅是他自己内心中的力量,他内心的情人。在弥尔顿那里,圣灵与力量是同一个概念,它们统一在弥赛亚的隐喻中,并危险地紧密结合在弥尔顿本人的形象之中,这个形象不仅是那个在诗歌中言说的声音,而且是那个比圣经更旧的旧约全书和更新的新约全书的创作者。像乔乞姆一样,但丁书写的是第三个启示录;弥尔顿则更加雄心勃勃,他书写的是一部甚至先于摩西的启示录,因此也就必然比任何一个对手更具有当代性。
我们这个贫瘠的时代玩弄着作者之死的说法,而弥尔顿的那个永远的权威形象,那个活宝,则对我们的这种做法虎视眈眈,他才是那种既放大文学边界却又憎恨作者的永恒的篡位者,在他的面前,我们今天的那些人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撒旦不是我们的夙敌,而是我们的故交,撒旦大叔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化身,因为他迄今仍是从伊阿古、爱德蒙到韦斯特笔下的施里特等所有反派角色中最伟大的一个。我们现在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撒旦大叔的困境;如果你是一个老到的文学批评家,像我的那个悲伤的自我一样,你每天都会步履蹒跚地吟咏着下面的诗句,这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气氛的诗:
虽然在地狱的底层,
仍有更深的一层张着大嘴
在等待把我吞下去;同那相比,
我目前的地狱简直是天堂了。
……
既是最具颠覆精神的革新家,又是最正统的传统主义者!在时代的湍流——有许多正是他开创的——之间,哈罗德?布鲁姆始终镇定自若。他无畏世俗,自成一宗:他的诠释总能掐住命脉,如行走在高空的钢丝一般,令人屏息又激动万分。这部探讨强力诗人的强力大作,带来了一重强有力的批评洞察。
—— 马克·菲尼《波士顿环球时报》
阅读布鲁姆即是阅读经典,这是一种愉悦,亦是一种心灵启示。恰似他所欣赏的诗人一样,布鲁姆给我们带来了电光与火石——引领我们在黑暗中敏锐阅读的工具。
——《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