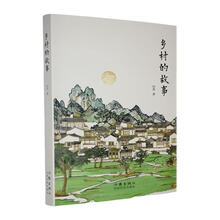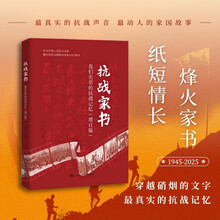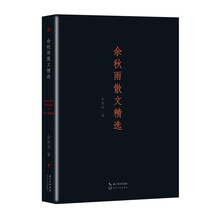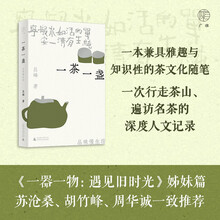她是1932 年离开越南回法国的,她和中国情人维持了一年多的感情,之后杳无音信。离开越南时她十八岁,此后再也没有踏上那片神秘的故土。那段感情对她而言正如那片土地,都是不可触碰的。它成为了回忆,成为了掩埋在心中的尘土,若非写作,也许此生都不会揭开。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杜拉斯对这段感情的态度,真相被扑朔迷离的故事遮蔽,就连晚年的杜拉斯自己,也将历史与小说混淆了。她需要的只是这段爱情,此生最眷恋也最难忘的爱情。
“在这里,重要的痕迹从未消失,而是躲藏在作品中,重新拼图。写作就像织布,编织图案,穿针走线,蔑视流逝的时间。”
中国人知道杜拉斯,很大程度归功于这部叫《情人》的小说,它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而在中国,有数万人阅读它。
中国人沉迷于这部小说的原因在于,法国女作家爱上了中国男人,而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
不管是杜撰还是事实,它真实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个读者都被这位法国少女的勇敢与沉着打动,爱上她的大胆,爱上她的冷漠绝情。许多年过去了,这段感情曾经尘封在历史中,被战争与岁月覆盖,更多的人步他的后尘,却很难造就一个真实的情人。爱情,只有这一次。
他一定很长时间无法和她相处,无法给她播下传宗接代的种子。他和那个白人姑娘的往事一定记忆犹新,她那躯体一定还在那里,横躺在床上。白人姑娘也一定长时间依旧受到他情欲的支配,使她冲动,情意绵绵而陷入愁思之中。后来这一天终于来了,一切都变成了可能。当他对那位白人姑娘的情欲发展到无可忍耐的地步时,在那狂热之中,他一定会重新发现这个白人姑娘的形象,而他正是怀着对这个白人姑娘强烈的欲望和另一个女人结合了。他一定是通过想象来使自己从这个女人身上获得满足,并且也是通过想象去完成家庭、天意以及北方的祖宗对他所赋予的使命:传宗接代。
——《情人》
灵魂深处的痛苦与绝望,往往在于心的封闭,无法对别人慈悲。
她去看他的婚礼,他穿着传统的中国服饰,新娘由轿子抬着,过河而来。他年迈的父亲脸上洋溢着舒心的笑意。她坐在栏杆上,在一群人中间远远地看着他。他扶新娘下轿,抬头瞥见她,只是一眼,无言的结局凝定在相视的眼中。
她想象他的中国妻子:“也许她已经知道原先这个白人姑娘的存在。她曾经用过沙沥当地的女仆,而这些女仆都知道这段历史,她们一定会对她透露一点风声,她一定会很痛苦。她们两个可能是同岁人,十六岁。在洞房花烛夜,她是否看见她的新郎在悲伤落泪?而她会去安慰他吗?一个十六岁的姑娘,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未婚妻,能够体面大方地安慰一个成年人的这种应该由她承担的苦楚吗?谁晓得?也许她自己欺骗自己,也许她和他抱头大哭,一宵之间彼此没说一句话。后来,痛哭之后,情感终于代替了悲伤。”
十年,二十年,许多年以后,他将遗忘她,妻妾成群,儿孙满堂,和他的妻子相敬如宾。她希望他忘掉她,忘掉过去,忘掉他们的爱。她可以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离开这个地方,永远地离开。她记得他说的那句,我没有你的爱会死亡。可是,谁没有了谁不能活下去呢?依然活着,依然活得很快乐,痛苦被脸上的笑容掩盖,心在身体的最深处抽泣。没有关系,她会有无数的情人,他会有无数的女人。
四季如水一般流过,沉落,如同人的一生,最后凝固成坚硬的墓碑。荒原的尽头,最后一朵花正在凋谢,绿和黄交织的土地上,两个人的相视就像这令人窒息的光阴,诠释着生命深处,最后的悲哀与留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