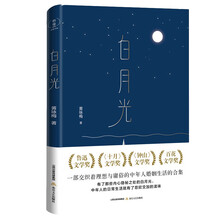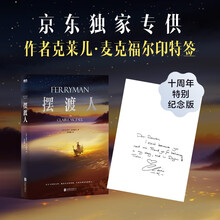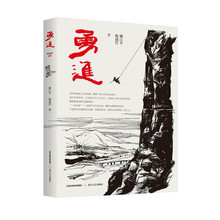说来也巧,闻莺到青山县的那天,正是青山县令过寿。温良远是出了名的清正廉洁,爱护百姓,自然就也受百姓爱戴。
那天青山县县衙大门敞开,筵席从衙门院子里摆到了十里长街上,入席的都是些寻常百姓。县衙张灯结彩的,甚是热闹。
闻莺抱着空瘪瘪的肚子也打算去大吃一顿,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闻莺从家里逃出来,身上没带多少银子,每月她爹给的月钱虽不少,但她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又总爱赏给下人,所以总是存不住钱。
逃婚这事又不能让旁人知道,闻莺收拾了几件金玉首饰便匆匆逃了出来,可首饰那东西,贵重是贵重,关键时候又不能当银子花。她也不敢随便把它们当了,生怕以她爹的精明劲儿,从当铺顺藤摸瓜,再把她揪回京城。
于是那些首饰就只能安安静静地躺在她的小布包袱里。一路跟着镖局那些人,吃住省了,可别了他们,到了青山县,荷包里的那点小银子总要省着花。
闻莺想,从今天开始,一天能吃一顿就绝不吃两顿。能省下来的银子,就绝对不能花!
衙门里挤挤攘攘的,坐的全是百姓,闻莺轻而易举就溜了进去。
百姓们正等着给县令祝寿,于是闻莺就开始在县衙里逛荡,四处打量了一下鼎鼎大名的青山县衙,心想原来也就是普通衙门的样子,没爹描述的那么好嘛,反而很破,尤其是后院的那个小花园,草长得简直都比人高了。
简直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已经荒废了的破院子。
边逛边嫌弃着,闻莺一不留神就顺着香气逛到了厨房。
厨房里准备菜肴的师傅很多,闻莺顺了只烧鸡,蹲到花园的一座假山后面开始吃。
吃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她今后的人生。
小时候,家里请过教武师傅,教大哥一些基本功。柳权自小就宠爱闻莺,她闹着要学,于是便让她和柳埕一起学。
可闻莺毕竟是个姑娘,娇里娇气的,学了一段时间就不想学了,柳权便又问她想学什么,女孩子家总要有一样能拿得出手的。
可是闻莺哪里晓得自己要学什么,她娘又不管她。于是柳闻月学什么,她便也跟着学什么。
到了最后,柳闻月什么都学会了,她学什么都坚持不下来,总是学了个半吊子,什么都会有一点儿,可什么都不精。
这下离开柳府,自己一个人在外面,闻莺根本就不晓得自己能干什么,只好哀怨地啃着鸡腿叹了口气。
闻莺刚叹出一口气,就听见有脚步声。她好奇地顺着假山的缝隙向外望,只见有个小厮抱着一大坛酒,酒坛上面还贴了一个硕大的“寿”字,正步履匆匆地往前院走。
应该是祝寿酒,估计是要开饭了。闻莺想。
小厮正走着,从后面小跑着跟过来一个人,拍了拍他,两人不知说了什么,小厮把酒交给了后面跟着过来的那个男人,小跑着又原路返回,估计是回厨房了。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闻莺低下头准备继续啃鸡腿,却看见跟过来的那个男人把酒坛往地上一放,揭开盖子,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打开纸包撒了进去。
做好之后男人把盖子盖回去,眼神犀利地扫了一下四周,闻莺吓得忙把脑袋缩到假山后面。
男人环顾了一会儿,瞅着四下无人。这才又抱起酒坛沿着小路往前院走。
闻莺这下也无心吃鸡了,若是下毒的话,这么一大坛寿酒别说温良远会喝,来吃寿宴的百姓们也会喝。
温良远从官这么多年,虽说奉公守法,但难保不会得罪一些大的商号和名门望族。若真是想毒死他,岂不是那么多百姓也要无辜陪葬。若不是下毒……
闻莺想得多了起来,脑子自然也开始乱,刚刚那个男人面相可怖,看着就像个亡命之徒,就算那些粉末不是毒药,也绝非是好东西。
闻莺懊恼地踢了下脚边的那只鸡,这事怎么就让她撞见了呢。青山县离京城也不算远,她若是在这里管闲事管出名堂来了,难保不会有什么风声传到她爹爹的耳朵里,到时候她岂不是白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跑出来?
可是,人命关天,这闲事也不能不管。闻莺纠结地想了想,站起身拍拍屁股,决定先去前院看个究竟。
前院热闹得简直不能再热闹,闻莺跑过去的时候,祝寿酒已经被放在了主位上。
主位上坐着一个穿着布衣的白面男子,一看就是个弱不禁风的羸弱书生——这就是温良远?
好白啊。这是闻莺对温良远的第一印象。
看着倒是很朴素,明明是个特别有油水赚的官位,被他当成这样,也算是不容易了。
就在闻莺感叹的时候,温良远已经站了起来,拱手对下面席位的百姓说:“温某在这青山县就职也三年有余,席下各位对温某诸多照拂,如今又如此破费为温某祝寿,此等恩情温某铭记于心,定不负众望。”
立刻有个人站出来说:“温大人这么客气就是见外了。咱们青山县里里外外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客气什么!”
接着就是一堆人迎合道:“就是就是,温大人,客气什么。”
温良远揭开酒坛的红盖子,把比人腰都粗的酒坛轻轻一掂,抱起来往自己的酒碗里倒了满满一碗。
看着挺瘦,力气真大。这是闻莺对温良远的第二印象。
能把青山县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这个温良远若真没两把刷子也说不过去。果然是人不可貌相。
温良远端起酒碗:“那温某就先干为敬了。”
底下百姓一齐喝彩。
这时有两个衙役抬起酒坛,去给院里的百姓倒酒。
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副场面。
然而温良远刚把酒碗凑到嘴边,酒碗忽地被不知从哪个方向射来的石子震破,碗裂成几瓣,落到了地上。碗里的酒也跟着洒下,在地上泛起白沫。
百姓都被这一幕吓到了,有几个站在前面的,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手里的酒碗,手一抖,登时好多酒碗落到地上。
无一例外,所有的酒里都有毒。
闻莺看着眼前的场面,呼出一口气,把手里的弹弓揣进怀里收好,正准备功成身退,却感觉似乎有人在看她。
她生怕被人发现,立刻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四周是一派乱糟糟的局面,百姓们被吓得乱作一团,闻莺这才舒口气,从身边的酒席上又顺了只鸡,大摇大摆地往大门走。
温良远被吓得脸色更加白了,紧张地拽着身旁的蓝衣服少年:“小五,这……”
被唤作小五的人倒是比温良远镇定多了,有些嫌弃地掰开温良远的手,说:“有人下毒,你得赶紧安抚百姓,立刻关闭县衙所有大门。孔大,你带些人手把衙门围起来。孙二,你去厨房,把凡是碰过寿酒的人都带过来。”
“是。”两个满脸横肉的魁梧大汉领了命忙活去了。
小五自己迈开了步子也要走,温良远还处在受惊状态,忙拉住他:“小五,你干吗去?”
小五没理他,再次把他的手掰开,无情地迈开步子走了。
闻莺才懒得管这些,叼着鸡腿继续怡然自得地往门外走,不料刚走到大门口便被人拦了下来。
“不好意思小兄弟,衙门里有人下毒。现在禁严了,谁都不准出去。为了安危着想,小兄弟还是先留步吧。”
留步就留步,反正下毒的又不是她。闻莺十分好说话地叼着鸡腿又往回走,走了没两步,撞上一个人,闻莺好心地伸出爪子拉住他,含着满嘴的鸡肉,含糊不清地说:“兄弟,禁严了,不让出,回吧。”
那人神色复杂地盯着她拉住自己衣服的手,眉毛皱了起来。
闻莺顺着他的视线看了看,干笑着把手松开。蓝色绸缎料子的衣服上,沾上了一个大大的油手印,隐隐还散发着烧鸡的香味。
闻莺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把手往自己的粗布衣服上又抹了抹:“那个……这位兄弟,对不住啊。你这衣服挺贵的吧?”
眼前这人,一副贵公子的样子,就是面色黑了一些,两道眉毛较皇上的更为英挺,只不过板着一张脸,毫无表情,不像那个人会笑,就算不笑也很温暖。
闻莺猛地摇了摇头,怎么会想起皇上呢!没出息!
贵公子有些嫌弃地看了看闻莺擦手的动作,以及她手里还剩的那半只鸡,扬声说:“来人,此人有下毒的嫌疑,抓了。”
闻莺还没反应过来,胳膊便被闻言跑过来的两个衙役揪住了。
闻莺怒了:“哎!蓝衣服,不就是弄脏了你的衣服吗,赔你一件就是了,你抓人干吗!你这是公报私仇!我要告你!”
蓝衣服没给她任何回应,她就这么被押到了温良远的面前。
“大人,我冤枉啊!这个人他公报私仇!大人,你是青山县的父母官,一定要为草民做主,革了他的职啊!”闻莺泪眼汪汪地看着温良远。
温良远有些无奈:“小五……”
小五很酷,抱着肩站在闻莺身边面无表情,并且一言不发,似乎在想事情。
闻莺被两个衙役按着跪在地上,恶狠狠地仰头瞪身边的人,心想,就叫小五,这么难听的名字,拽什么拽!
有个衙役跑过来通报:“大人,不好了!属下刚才去厨房问有谁碰过寿酒,大家说这坛酒是今早从天香楼运过来的,运来后就放在那里,没人动过。可刚刚属下去盘查的时候,厨房里的人说,送酒过来的那个小厮抱着酒坛出去后就再没回去过,属下一路查探,发现那个小厮死在了后院小路上。”
温良远终于有了点儿一县之主的样子:“走吧,去看看。”
“等一下。”小五再次开口,转过身对这院子里一堆议论纷纷的百姓说,“诸位乡亲,今日发生此事实在是抱歉,诸位去守门衙役那里禀明身份,就可自行离去。”
温良远看了看院里的百姓:“万一下毒之人就在这里面呢?”
小五用“你是白痴”的眼神瞥了一眼温良远,抬起步子往后院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指了指还跪在地上冲他扔眼刀子的闻莺:“带着他。”
闻莺被押到后院,冲温良远嚷了一路的“冤枉”,温良远只是挠着头讪笑:“小兄弟再忍忍,等本官查明真相,定还小兄弟一个清白。”
无端就被当成了嫌疑犯,好心没好报。闻莺现在觉得十只烧鸡都不能让她的心情好起来。
闻莺心里这么想着,继续恶狠狠地瞪走在自己前面的小五,然后没好气地问身边一个衙役:“那个看起来拽得不能再拽的人是谁啊?”
衙役答:“是我们师爷。”
就是个叫小五的师爷,牛气什么啊。闻莺气冲冲地哼了一声,走在前面的人立刻回头看了她一眼,闻莺很没有出息地被那个眼神吓得低下了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