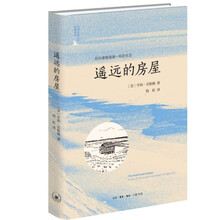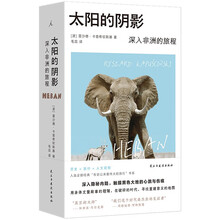一病难释怀
消炎药成为我随身背包中的必备物,从2011年国庆节一直到2012年清明节的前夕,足足六个月。
在这六个月之中,无论是在外地出差,还是在办公室,亦或是在家中,在公园里,说不定哪天因腹部不适,就会借用消炎药来缓解隐隐的痛。效果是明显的,服用消炎药后的一两天症状几乎消失为零。在消炎药的作用下,一次次的隐痛被镇压下去,掩盖起来,也使得我的恶性肿瘤继续生存并发展了半年时间。
2011年9月15日,强烈的腹部疼痛把我从睡眠中“拉”了起来,这种剧烈的痛感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身体疼痛,叫人忍受不了。即使对我这样一个身体素质一向觉得不错的中年男人来说,也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
“深呼吸,保持放松,突然的疼痛感说明不了什么。”我这样安慰并调整着自己。
事实上,我忽视了一个重要线索,我的腹部不适已经有几天了,只是没有引起我足够重视而已。这是后来我回想病情时才注意到的。
疼痛感略有缓解,但很快又发作起来。
额头慢慢渗出了汗。
迅速地利用手机在互联网中搜寻。
右下腹部疼痛,伴随着间断的肠鸣。
疼痛感逐渐向腹部中间部位移动,痛感时重时轻。
人体腹部结构图、阑尾炎的症状、……,移动互联网瞬间就能带来巨大的信息量,我似乎为自己的高效率感到满足。
阑尾炎,坚定的答案浮现出来。我一定是患上了阑尾炎。
这是我通过互联网的查询、比照而给自己做的判断。也因此,我异常冷静,疼痛也有很多缓解,也就没有惊扰因照顾女儿分屋而睡的爱人若凡。
一大早,若凡陪我一起来到了靠近万寿路北口的某总医院。
门诊楼大厅靠近入口处的医导员拦住了我们。
“挂哪个科的号?”
“我可能得了阑尾炎。”
“什么症状?”
“这里疼(我指着上腹部),疼痛是从右下侧逐渐转移过来的。”
“这不像是阑尾炎。”
就在这一问一答中,我们匆匆离开了医导员那里。
医导员不足二十岁的年龄,语言中充满了疑虑。一向不爱去医院甚至对医院有些反感的我,自然对她的话充耳不闻。我时常批评自己的这种自负,对当时没能给予那位医导员足够的耐心和尊敬深感歉疚和不安。
医生简单问了情况,我描述的似乎更简单。
“我应该是得了阑尾炎。”我又自作主张地表明了自己的判断。
中年女医生给我做了“压痛感”、“反跳痛”检查。右下腹部有无压痛感、有无反跳痛是临床检查是否患阑尾炎的手段之一。显然,我的“压痛感”和“反跳痛”是明显的。
“在我们医院做手术吗?”中年女医生平静的说。面无表情甚至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
我犹豫了。
在这个用仪器检测结果为诊断依据的年代,未经任何B超、验血等最简单检查就确定了我的“阑尾炎”。并且昨天还活蹦乱跳的我马上就要做手术,一下子来的太突然。
虽然自己断定是得了阑尾炎,但一经医生确认,突然有一种侥幸的想法冒了出来:会不会明天就会好了?瞬间又产生了另一种想法:这样就手术是不是太草率了?
这些想法的瞬间出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对中年女医生的不信任,不管她的医术如何,只凭她的态度就无法让我相信她。虽然我们不能强求每位医生对病人的态度都能做到和善,因为很多医生在半天出诊时间里就要接待几十甚至上百位病人,不论是对精力、体力还是状态都是很大的考验,但在我的理解中,至少要对我给予必要的病情诊断介绍,特别是说明如果要手术,是否住院以及住院时间等基本信息,而不能仅仅一句“在我们医院做手术吗?”就让我做出决定。
“我们再商量一下。”说完这句话,我和若凡一致决定去位于东单的某著名医院看一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