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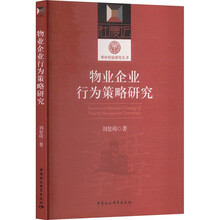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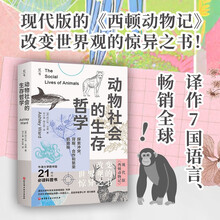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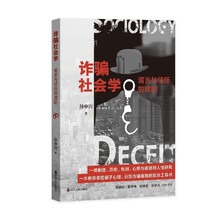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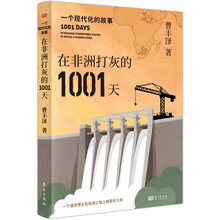
诚实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就在于谎言是普世现象,从政坛精英到市井小民,从商界巨贾到谍海特工,它成为生活的潜在主线。
保罗·埃克曼的这本《说谎》一版再版,被欧美诸多执法机构奉为刑侦学教材。它告诉读者,人们是如何说谎,为何说谎,说谎时何有何表现;如何识破谎言,识破的可能性以及利弊;如何创造和增进识破谎言的机会。
对于必须娴熟人际互动,了解嫌疑人性格特质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与警察而言,这是一本强化职能的教材;对于需要洞悉人心,长于沟通的心理医师、社会工作者与咨询专家而言,这是一本很好的人际互动宝典:对于极欲防止被骗的市井百姓而言,这更是一本可以减少上当机会,防范诈术的实用指南。
第一章 导言
有些谎言反而是利他的,虽然其数量绝不像说谎者所宣称的那样多。
但是,说谎者绝不应轻率地以为,受骗者都愿意被蒙在鼓里;抓谎者也绝不应轻率地以为.自己有权说破每个谎言。
1938年9月15日,一场最龌龊、最恐怖的骗局揭开了序幕。这一天,德国总理希特勒(Adolf Hitler)与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首度会晤,全世界都在观望,这也许是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希望。(六个月前,希特勒的部队已经入侵奥地利,将之并入德国版图,英、法两国除了抗议之外,根本束手无策。)9月12日,即与张伯伦会晤的三天前,希特勒提出由德国兼并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土地的要求,并计划在其境内煽动暴乱,同时秘密调动德军,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发动攻击的部署要到9月底才能完成。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能够让捷克斯洛伐克再拖延几个星期部署防御,他就可以发动闪电攻击;为争取准备的时间,希特勒一面秘密调动部队,一面承诺张伯伦,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同意他的要求,和平就可以得到保证。张伯伦信以为真,说服捷克斯洛伐克暂时停止调动部队,准备与希特勒展开谈判。与希特勒会晤之后,张伯伦在写给其妹妹的信中说:“在他的脸上,尽管我看到了冷酷与无情,但我的印象是,这个人会信守承诺……”五天之后,张伯伦在国会发表演说,面对他人质疑希特勒的承诺,他依旧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说他与希特勒亲身接触的结果,让他觉得希特勒是个“言出必践的人”。
15年前,当我刚开始研究说谎时,我绝不会想到我的工作会与以上这种可怕的谎言有关。只有在从事与精神疾病患者有关的工作时,我才偶尔想到,它或许有用得上的地方。我最初开始研究谎言,是在指导治疗医师的场合,谈的大多是我的研究心得:面部表情普世皆同,手势则因文化而各异。当时有学员提问,从病人的非口语行为上,是否能够知道他是在说谎?。一般来说,这本不是问题,但是,当一个病人因自杀而住进医院,表示自己已经没事时,问题就来了,患者一旦出院,缺少医院的看护,每个医生都会担心,病人说自己没事,会不会只是在欺骗他们?医生这种在业务上的疑虑,引发了人类交流中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即使心绪极度不宁,人们是否还能神色自若地说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否可以从非口语行为上找到破绽,揭露言辞背后隐瞒的心思?
我调出对精神病患者的访谈影片,看看能否找到说谎的案例。拍摄这些影片本来另有他用,即要从病人的表情与动作,诊断精神失调症患者的病情与类型。当我把目标转移到说谎的情况时,发现许多影片真的透露着说谎的迹象,问题是,如何才能予以确认?幸运的是,其中有个个案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访谈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说明了一切: 玛丽,四十二岁,家庭主妇。三次企图自杀,最后一次非常严重,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只是经人意外发现而送医,才把她从鬼门关前抢救回来。她的故事是典型的中年妇女抑郁症,孩子长大了,不再需要她,丈夫则忙于事业,使她生活顿失重心,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刚住进医院那段日子,她无法料理家务,又睡不好觉,几乎整天独自以泪洗面,经过最初的三个星期药物治疗与群体治疗,她看起来恢复得不错,精神开朗起来,也不再谈起自杀的事情。在那次访谈的影片中,她告诉医生,觉得自己好多了,请求放一个周末的假。就在医生同意准假之前,她却突然承认自己在说谎,事实上她仍然很想就此了断。玛丽又住了三个月之后,病情大有改善,虽然一年后又复发过一次,但整体来说,没再住过院,维持正常多达数年。
玛丽接受访谈的影片,播放给精神科医生与心理学家看,结果大部分人都被骗了,其中甚至不乏经验丰富的老手。。这段影片,我们研究了几百个小时,放了一遍又一遍,用慢镜头检视每个动作与表情,想要找出其中任何可能的说谎线索。在一个片段中,医生问她未来有什么计划,回答问题前,她迟疑了片刻,脸上闪过一丝绝望的表情,但由于太短暂,在前几次的检视中都被忽略了。在这种非常短暂的微表情中,可能隐瞒着某种情绪,一旦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便继续寻找,果然找到更多,基本上都是一闪即逝掩藏在浅笑中。我们也发现一种碎动作,当她告诉医生自己把问题处理得多好多好时,不时出现轻微的耸肩——不是完整的动作,而只是动作的一部分。只有一只手有动作,旋转一下,或者双手是静止的,而肩膀微微抬起一下。
我们还看出了其他非口语的说谎线索,但却无法确定究竟真的是有所发现,或者只是出于想象。如果确实知道某人说谎,某些完全无辜的动作似乎就是可疑的,但是,只有客观的评估,即在不受对方是否说谎这一信息影响的条件下,才能检验我们的发现;此外还必须确定,说谎线索并非研究对象的习惯动作。如果每个人泄露出的说谎线索都一样,对抓谎者来说就省事了,但问题是,说谎线索总是因人而异的。我们以玛丽的谎言为模型设计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研究对象极力去隐瞒在说谎时感受到的强烈的负面情绪。当观看一个非常消极的影片时,譬如展现了血淋淋的外科场景,我们的研究对象们不得不隐瞒他们的悲伤感、痛楚感和厌恶感,并且使研究者认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个影片,而是欣赏了一片美丽花丛的影片(我们的发现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有所描述)。
一年过去了,我们的说谎实验仍在起步阶段,此时另外一批对其他类型的谎言感兴趣的人找上门来,想知道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看看是否可以用来抓出涉嫌间谍案的美国人?过去几年间,针对医患之间说谎的行为线索,我们所做的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科学期刊上。因此,相关的征询也不断找到我们:是否能够训练内阁官员的侍卫,从步态与举止上识破恐怖分子的暗杀倾向?是否能够指导联邦调查局如何训练探员,以便更有效地识破犯罪嫌疑人的谎言?到后来,甚至有人问我,是否可以协助政府高层的谈判代表,识破对手的谎言?或者问我是否能从帕特里夏·赫斯特(Patricia Hearst)参与银行抢劫的照片分辨出她当时是否自愿?诸如此类的询问,我已习以为常。在过去五年当中,这方面的研究更引起国际上的注意,两个美国的友邦国家派代表跟我接触;而当我在苏联演讲的时候,自称是负责问案的某个“电气学院”的官员也找上门来。
我并不为这些关切感到愉快,我担心这些研究成果受到滥用,受到不加批判的、迫不及待的应用。大部分犯罪、政治或外交的谎言,未必可以找到非口语的说谎线索,有时纯粹靠直觉,真要问我,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定得讲出个名堂的话,就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人在说谎时,为什么一定会犯错?并非所有的谎言都会穿帮,有些谎言天衣无缝,面部的表情太僵、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声音突然变调……这些说谎的行为线索全都不会出现。但我确知,只要是说谎,就一定有破绽,哪怕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照样会被他自己的行为给出卖。要想知道什么时候说谎会成功,什么时候会失败,如何辨识谎言的线索,以及什么时候根本不值得说谎,你必须要了解谎言与谎言之间、说谎者与说谎者之间以及抓谎者与抓谎者之间的千差万别。
希特勒对张伯伦说的以及玛丽对她的医生说的,都是致命的谎言,是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的,两个人都把未来的安排藏在心底,也都装出某种并没有感受到的情绪作为谎言的核心,但是两个人的谎言之间却有巨大的差异。希特勒是我后来将谈到的天生说谎家的典型,比起玛丽来,除了天赋的技巧外,他在骗人方面的实践经验可说是不知要丰富多少倍。
希特勒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他所欺骗的那个人甘愿受到误导。希特勒谎称没有战争计划,只要按照他的要求重划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即可。张伯伦不仅相信,而且可以说是一厢情愿地盲信,因为,如果他不相信,就等于承认自己的绥靖政策失败,而且英国的利益受损。政治学者沃尔施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分析军备竞赛的骗局,所持的就是这一观点,谈到德国违反1936年的英德海军协议时,她说:
施骗方与受骗方都在赌,使得错误持续地发展下去,双方都抱有幻想,以为对方不会违反协议。希特勒操弄英国害怕军备竞赛的心理,成功达成一项海军协议,已经使英国(在未与法、意等国磋商的情况下)默认了《凡尔赛和约》的改写;当新的协议又受到破坏时.这种害怕军备竞赛的态度,使英国再度乡愿地不去面对违反协议。
在许多骗局当中,对于说谎者的破绽,受害者总是故意不去面对,一厢情愿地往好的方面设想,害怕谎言一旦拆穿,可怕的后果将难以收拾,于是成了骗局得以持续下去的帮凶。丈夫故意不去面对妻子的外遇,至少可以暂时免掉戴绿帽子的羞辱以及离婚的结果;对妻子不忠的行为,即使心里有数,却不予拆穿,为的只是避免一旦摊牌,事情就失去转圜的余地,只要什么都不说,即使希望十分渺小,依然可以抱着一线希望——或许只是自己错怪她,她根本就没有外遇。
并非每个受骗者都因为一厢情愿,有时对谎言的线索视若无睹或予以纵容,并不会带来什么损失。有的人抓谎,只是为了抓谎而抓谎,警察审讯犯罪嫌疑人,唯一可能的损失就是被骗,跟承办贷款的银行职员一样,对他们来说,揭穿骗局与厘清事实都只是善尽职责而已。误信谎言或予以拆穿,被骗的一方通常有所得,但也有所失,只不过所得与所失往往是不相称的。玛丽的医生相信她的谎言,所冒的风险并不大,如果她真的好了,不再抑郁,医生可能因此而得到某种声誉;万一她并未真正好转,医生的损失也不大。与张伯伦不同,医生的整个职业生涯并没有风险,因为他并没有对患者被治愈了的判断作出公开保证,毕竟一旦发现患者说谎,该判断就会被证明是错的。那样的话,他受到欺骗时的损失将远大于患者诚实时他所得到的收获。而对于张伯伦来说,1938年的一切显然都太迟了,如果希特勒所言不实,如果除了战争,无法阻止他的侵略,那么张伯伦的政治生涯将就此告终,而他自以为可以阻止的战争也将就此爆发。
除了张伯伦的一厢情愿之外,希特勒的谎言之所以能够成功,还在于他不需要掩饰任何强烈的情绪。大多数谎言之所以穿帮是因为压抑的情绪泄了密,和谎言有关的情绪越强烈,情绪的类型越多,就越容易出现某种形式的行为线索。希特勒毫无罪恶感,罪恶感这种情绪使谎言倍加脆弱,不仅它本身能泄露形迹,而且会使人因内心不安而犯错,以致被人识破。在希特勒的有生之年,英国曾让德国饱受战败的耻辱,面对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他当然一点罪恶感都没有。与玛丽不同,希特勒既没有与对方共享重大的价值观,也没有任何尊敬或
钦佩对方的感情负担。玛丽必须掩饰强烈的情绪,一则是她想要自杀的绝望与焦虑,二则是对医生说谎,她有一万个理由产生罪恶感,因为她喜欢并尊敬他们,深知他们只是要帮助她而已。
正因为如此,面对有自杀倾向者或不忠的配偶,想要找出说谎的行为线索,远较面对外交人员或双面间谍来得容易。但是,并非所有的外交人员、罪犯或谍报人员的谎言都无懈可击,有时候犯错在所难免。按照我的分析去做,人们可以评估出,发现说谎线索或者因没发现而被误导的可能性各有多大。对于那些想要识破政治谎言或犯罪谎言的人,我的忠告是:关键不在于是否忽略了行为线索,而在于保持高度的警惕,知晓风险并抓住机会。
虽然关于说谎的行为线索已有一些证据,但仍不十分成熟。针对说谎方式、说谎原因以及谎言的瑕疵,我所做的分析都是根据相关的谎言实验,以及史实或小说所进行的,但是这些理论仍有待进一步的实验和批评意见来检验。现在之所以不待一切最终确定就付梓成书,实在是因为抓谎者不能再等了,为失误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大,抓出说谎者的非口语线索已经刻不容缓。“专家”不熟悉采证与诘问技巧,就仓促披挂上阵参加陪审团和求职面试,其间的风险不问可知。有些使用测谎仪的警察与专业测谎人员,虽然学过说谎的非口语线索,但据我所见,他们所用的训练教材有半数信息都不正确。海关官员都要上一门课,讲授如何辨识走私的非口语线索,据称就是拿我的研究作为教材,虽然我一再要求过目,所得到的回答却一成不变,每次都是“我们会马上回复您”。至于谍报人员的情况则不得而知,因为他们从事的都是秘密工作。六年前我曾受国防部之邀,讲解抓谎的机会与风险,知道他们对于此类问题甚感兴趣,但自那次以后,虽然风闻有关工作已进行,我也曾致函相关人员,然而结果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无可奉告。我所担心的是,“专家”闭门造车,而学界则吹毛求疵,本书应可为他们厘清抓谎的机会与风险问题。
另一方面,撰写本书的目的并非仅仅针对重大谎言,我深信,检视说谎或说实话的方式与时机,将有助于理解很多人际之间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中,与谎言无涉的机会极少,生活中总是难免会说谎,譬如父母亲跟孩子谈到性,认为孩子不宜知道的,往往以谎言打发。反过来说,由于父母的排斥,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对性方面的冒险,也总是能瞒就瞒。此外,在朋友(甚至最好的朋友)、师生、医患、夫妻、律师与委托人、业务员与客户等关系中,谎言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谎言之于生活是如此普遍,它几乎涉及人类的一切事务,所以多予理解实属必要。这种论调或许有人嗤之以鼻,认为凡是说谎就应该受到谴责,对此我不敢苟同。要求人们在任何人际关系中都不得说谎,未免简单粗暴;要求对于任何谎言都应予以拆穿,也未免会欺人太甚。专栏咨询家兰德斯(Anne LaJlders)有一句话说得好:“真相同样可以拿来伤人,甚至使人痛不欲生。”尽管谎言也伤人,但并非全都如此,有些谎言反而是利他的,虽然其数量绝不像说谎者所宣称的那样多。某些社会关系,全因彼此保守秘密而得以相安无事。但是,说谎者绝不应该轻率地以为,任何受骗者都愿意被蒙在鼓里;抓谎者也绝不应轻率地以为,自己有权说破每个谎言。某些谎言是无害的,甚至是人道的,揭穿某些谎言,可能对受骗者或第三方造成羞辱。但这一切都要仔细地加以考虑,并且事前需要讨论很多其他问题。下一章我们将从谎言的定义开始,讨论谎言的两种基本形式和说谎线索的两种类型。
……
第三版序
致谢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谎言、破绽与说谎线索
第三章 谎言何以穿帮
第四章 言辞、声音、身体行为与谎言
第五章 说谎的表情线索
第六章 陷阱与预防措施
第七章 测谎仪
第八章 估谎
第九章 20世纪90年代的抓谎
第十章 公共领域的谎言
第十一章 新进展与新想法
结语
附录
校者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