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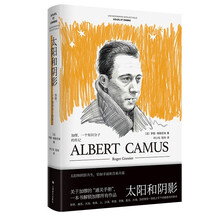

《萧红印象:记忆》是对于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呼兰河传》的作者萧红个人的忆述。叙述者有同时代人,也有晚生的作家;有萧红的情人、亲属、朋友、同学。不同的眼光看同一个人,层次感和丰富性突显。
两个月以前,从朋友那儿看到鲁彦给他的信里有这样的一句:“闻萧红于香港陷落时病死。”在战争时期,一个人的死,原是很平常的,尤其是病死。这颇像秋风狂吹落叶,不大使人注意——战争是把人的情感磨折得僵化了。然而,倘死者是你的亲人,朋友,你却不会这样无动于衷,总还是要感到悲哀的。当时我辞别了朋友,带了一颗沉重的心走回家来。我只能以“希望”安慰自己,就是希望这不幸的消息是讹传的。及后陷港友人相继脱险归来,直接证实了萧红的死讯,希望破灭,于是我为不幸而死去的友人低垂下头。
最近八九年来,在中国女作家中比较勤谨写作的是萧红。她不断的以作品和读者对面,和历史对面,并在中国文艺园地上开放着还算健康美丽的花朵。关于这一点,正直的读者,大概是不会否认的。现在她死了,为贫病所逼,死在恐怖的香港。这是中国文艺界的损失。她正年轻,死得太早了。
1934年夏天,由于寂寞,我离开了烟台——那曾经生活了三年的东山葡萄园和渤海滨,到青岛去,参加友人刘君刚接办过来的一个日报(《青岛晨报》)的编辑工作。就在那个时候,我同三郎(萧军)、悄吟(萧红)、老李(舒群)认识了。他们从东北逃亡出来不久,和我们一道工作。也许因为我们都有着以文学为事业的野心,并且都正在下死劲写作着的缘故,在报馆里的同人巾,我们相处的比别人更好,更投契。我是住在报馆里的,三郎和悄吟则另外租了一问房子,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
三郎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于是,我们徜徉在葱郁的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而在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大惊小怪的四处游泅着。悄吟在水淹到胸部的浅滩里,一手捏着鼻子,闭起眼睛,沉到水底下去,努力爬蹬了一阵,抬起头来,呛嗽着大声喊:“是不是我已经泅得很远了?”
“一点儿也没有移动,”我说,“看,要像三郎那样,球一样滚动在水面上。”悄吟看了一看正在用最大的努力游向水架去的三郎,摇头批评道:“他那种样子也不行,毫无游泳法则,只任蛮劲,拖泥带水地瞎冲一阵而已……我还有我自己的游法。”
她又捏着鼻子沉到水底下去。我第一次看到悄吟的作品,是在我们的报纸副刊(三郎编)上发表的一篇小说《进城》。清丽纤细,然而下笔大胆,如同一首抑郁的牧歌。由这篇小说作引子,我读着她和三郎合著的自费出版的《跋涉》。这是散文小品素描一类的东西(后来收入《商市街》里面)。属于悄吟部分的,其笔触清丽纤细大胆。我告诉她我的读后感,她睁着清澈润泽的大眼睛说:“啊,是这样吗?是不是女性气味很浓?”
“相当地。”我说,“但这有什么要紧?女性有她独特的视觉与感觉,除开思想而外,应该和男性不同的,并且应该尽可能发展女性底特点的,在她的作品里。”
其时她和三郎都在写长篇,他们工作得很有规律,每天按时工作按时休息,因之成绩很好。10月间,悄吟的长篇《生死场》全部完成;她朗诵一二节之后,我读着她的原稿。笔触还是清丽纤细大胆,好像一首牧歌。“怎么样,阿张?”一天下午我将原稿交还她,她这样问。“感想还好。只是全部结构缺少有机的联系。”
“我也这样感觉的。但现在为止,想不出其他方法了,就让它这样罢。”三郎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硬纸封面的原稿册,拍着它,并且翻动页面,如同一个孩子似的,傲然说:“哼!瞧我的呢。”
“那么,拿来读它呀。”“但是不忙,还没誊清呢。”他说着放回书架里去了。这是《八月的乡村》。报馆发生了问题,同人大体星散。我同三郎、悄吟一直将报纸维持到11月尾。我们穷得可以,吃不成烙饼、大菜汤了。将离开青岛那一天,悄吟同我将报馆里的两三副木板床带木凳,载在一架独轮车上去拍卖。我说:“木床之类,我们还是不要吧?”“怎么不要?这至少可卖它十块八块钱。”悄吟睁着大眼睛说:“就是门窗能拆下也好卖的。——管它呢。”
她大摇大摆地跟在独轮车后面,蹬着磨去一半后跟的破皮鞋。12月初,我们坐上一只日本船(好像是共同丸)的货舱里,同咸鱼包粉条杂货一道,席地而坐,到上海去。这是1934年末的事情。我们到了人间的天堂同时又是人间地狱的上海。我们住在一个廉价的客栈里,然后分头去找朋友和租房子。
第二天,我搬到少年时代的同学杨君的亭子间里去了。地点在“法租界”环龙路的花园别墅。所谓亭子间是长二丈多宽约丈余的小房子,只能放两张帆布床和一张写字台,三个人座谈就可以互相呼吸着从每个人嘴里呼出来的碳酸气。上海我是曾经短时期居住过好几次的。但每次都是住在较宽敞的旅馆里。现在住着这相同火柴盒子的亭子间,我这个在北方海洋地带生活惯了的人,好像一只从广垠的旷野被赶进牢笼里的野狼一样,烦躁而气闷,觉得一天也住不下去。
我安置好了行李,第二天回到客栈去,三郎和悄吟已经在拉都路尽头租到了房子,一早搬出去了。我一路问警察才找到了他们。这是近似郊外的贫民区域了,临窗有着菜园和篷寮。空气倒还清新。他们租的房子是新建筑的一排砖房子的楼上,有黑暗的楼梯和木窗。我探头向窗外一看,一派绿色的菜园映进眼帘。我赞美道:“你们这里倒不错啊,有美丽的花园呢。”
悄吟手里拿了一块抹布,左手向腰里一撑,用着假装的庄严声调说:“是不是还有点诗意?”我看一看她的伪装的脸色和傲视的清澈大眼睛,又看一看三郎的闭着的嘴唇,那边沿几根相同汗毛的黄胡子在颤动着,终于三个人爆发出大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