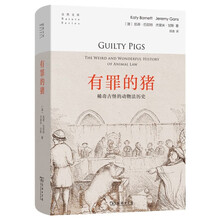1.如果我们将近代早期绝对主义国家的扩张逻辑,看作政治性的国家权力借助于“理性官僚制”的新装置不断地向社会基层渗透,攫取社会资源,摧毁社会内在的运作机理,形成由“高高在上的主权者”与“一盘散沙的诸原子化个人”所组成的国家共同体的话,那么英格兰普通法的发展史,更像是社会性权力不断地“逆生长”,向国家内部渗透,并逐渐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原则与结构的过程。英格兰宪政史,就是这样一部社会性权力向国家内部渗透的历史,其最具象征化意义的高潮,就是以议会代替国王,成为整个国家的最高主权象征。对于主权理论来说,议会主权就是一个由悖论构成的主权理论——一直作为主权之照看对象的被统治者,最后成了主权者本身。
2.革命未必总是代表着新旧两个世界剧烈的断裂。革命的这个含义仅仅代表着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大陆的经验,在英国的政治传统中,革命的本意反而是复辟,意味着某种传统的回归。英国革命中,查理一世和詹姆斯二世的重新掌握政权,可以被看作一种复辟,同样的,古老的宪政制度的重新建立,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更深刻与彻底的复辟,恢复的是自都铎王朝以来屡受威胁,且被斯图亚特王朝彻底破坏的普通法传统和议会传统。
哪怕是17世纪和18世纪西欧人普遍感受的物质财富的急遽增长与生活方式的剧烈改变,也很可能是古老传统的某些核心因素与诸如新大陆的发现等重大历史事件结合而催生出来的结果。因此,要研究英国的现代性转折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就要摆脱毕其功于一役、将现代性转型归结到激烈的政治革命的诱惑,而将目光转换到更深远的英国整个社会结构的观察与检讨之中。
3.对于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研究来说,对政治人物个性的研究并非无足轻重,因为关键性政治人物的个性、能力、婚姻关系等,都会对政治局势的演变与政治制度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约翰反复无常而又残暴的个性,招致了许多大贵族普遍的反感和怨恨,尤其是约翰残暴地杀害了自己的侄子亚瑟,更是对其统治的形象和正当性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这些都可以被看作1215年大起义和《大宪章》的重要背景。但约翰并没有传说中描述的那般无能,这恐怕也是真的。恰恰由于历史事件中关键性历史人物的重要性,人们往往容易对这些人物进行脸谱式的非黑即白的评价。与历史上许多评价甚高的伟大君主相比,约翰并不比他们更加反复无常或更加残暴,例如与约翰的先祖威廉一世相比,约翰未必更加残暴,但历史上对威廉一世的评价却要远高于约翰。同时,约翰顺利地继承王位,并且获得普遍的支持,恰恰证明了约翰作为君主的能力和手腕。
4.《大宪章》重申了英格兰传统的宪政传统,以及英格兰贵族和人民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并且作出了许多限制王权的规定。1215年英格兰《大宪章》的签订,逐渐演变成了英格兰的一种宪政传统,并且逐渐成了英格兰普通法的一种意识形态,即国王不服从任何人,但必须服从上帝与法律。这就构成了英格兰法律至上,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由此,英格兰普通法既构成了中央集权的核心成分,同时又构成了对中央政府权力过度扩张的有力限制。国王也就失去了用来打击地方贵族与乡绅势力的一个最有力的专政工具。
5.如果英格兰王室政府可以被比拟成一种处于雏形状态的中央政府的话,则普通法的机制使得地方自治社会的利益能够被反映到全国性机制形成的过程之中,从而使得全国性的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地方利益。通过普通法这个中介性设置,英格兰的国家建设从一开始就将地方性的因素和社会性的因素吸收进去,将社会内化到国家之中。这种社会与国家互相包含的机制,蕴含了此后被称为现代性现象的深层奥秘。
6.柯克与国王詹姆斯一世之间的斗争,可以看作英国革命的预演。就此后英国革命发生的过程与结局来看,最终取得胜利的是柯克,而不是国王。光荣革命先是象征性地剥夺了王权的绝对尊严,此后议会责任内阁制的发展,又实质性地将君主最依赖的行政权也剥夺了。失去了对行政权的控制,君主就真的变成一个象征与符号。又该如何理解柯克与国王斗争的这种象征性意义?柯克与国王之间的争论,特别典型地向我们揭示了两种政体逻辑之间的差异与针锋相对。
7.这种抽象机制,似乎并非如有文人情怀的真正哲学家韦伯,以及像霍克海默、福柯、哈贝马斯这样的现代西式文人所忧心忡忡地描述成的那样,成为吞噬人类最后一点自由的理性铁笼和怪兽。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抽象的机制,规制了绝对主义君主的恣意和贪欲,最大限度地捍卫着个人的自由。英美普通法宪政与欧洲大陆绝对主义理性官僚制,在20世纪的各自表现,以及两种主权国家内部人民的待遇,已经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8.理解宪法与宪政,尤其是理解英格兰宪法与宪政,是不能仅仅从政治的角度进行的。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理解英格兰宪法的历史,变得仅仅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或者说是留给法律人的工作,而且仅仅只是研究英格兰私法的历史,而英格兰的宪政史则仅仅被看作英格兰政治制度史。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英格兰宪政史研究的衰落。晚近二三十年的研究,在宪政史的研究中,重新引入了法律家的视角,又使英格兰宪政史研究重新焕发了活力。
9.英格兰宪政史研究的这种演变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启发我们:如果无法对英格兰普通法的历史与机制在理论层面提供现象学式的观照,就很难理解英格兰宪政的内在机理和运作逻辑。英格兰宪政的建设最初的表现,就是抽象的普通法机制与肉身化的王权之间的斗争和冲突。这种斗争和冲突最终以抽象的普通法机制战胜和淹没肉身化的王权为结局。通常所说的普通法宪政其实指的就是这个结局。因此,宪政的一个很根本的含义,就是政治统治的抽象化对肉身化的取代。相对于抽象的机制的统治,肉身化的统治拥有一个鲜明的优点,即主权者是会呼吸会笑会哭的活生生的人。因此,这样一个主权象征更容易唤起人们的服从感,更容易被臣民所理解。
10.“因此我情愿牢牢地盯住过去,以提醒读者我们是怎样过来的,目前的现象是怎样的,以及过去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从凯恩斯个人而言,戴着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光环而来,最后不得不理性却又屈辱地亲手埋葬大英帝国的荣耀时,其内心所经历的复杂情感,以及随同帝国荣耀一起殉葬的命运,这仍然是一个悲剧。然而,与历史上那些更为屈辱地灰飞烟灭的大帝国相比,能够在临死之前主动而又尊严地选择信得过的接班人,安排好身后事再放心地离开,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就此而言,大英帝国与凯恩斯的故事,似乎又改变了自古希腊一直到莎士比亚以来所形成的悲剧传统与观念。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