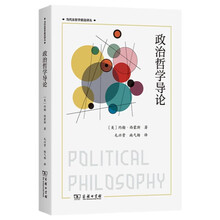一、传播所生成之社会以政治为轴心
以上我们浓墨梳理近乎于政治学常识的关于政治的认识,旨在说明,从历史的“历时态”看政治的生成过程,可以归纳为政治的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过程。这种过程既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历时展开过程,又是空间意义上的横向扩展过程。这种过程正是政治从无到有、从己到人、从私到公、从内到外、从一到多的通过“传播”这一根基性路径的生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在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特质”的基础上,与政治的本质取得同一性。可以通俗地表述为:没有不通过传播而形成的政治,正像不存在没有被统治者的统治者一样,即所谓的“政治即传播”。
这种看法的视角与深度,可能不同于现在人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解与解释,尤其是传播学学者对于政治传播本质的看法。我们没有具体展示所谓政治传播的历史形成过程,比如,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禹及上古时期《尚书》、《左传》等所记载的“口传”政治,先秦诸子百家的“说服”政治,秦汉时期的“书刊”政治,唐宋时期的“进奏”政治,元明清时期的“特务”政治;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的辩论修辞政治,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英法德的报业新闻政治,美国的宣导性政治,以及传播学创建后在传播技术与新媒体引擎下的说服政治、修辞政治、沟通政治等。
在我们看来,展示这样具体的对政治的传播过程,在理论上并不能揭示传播的政治本质和属性,而只能展示政治是怎样运用传播来实现自己的。毫无疑问,展示政治是如何运用传播手段,还是在政治范畴中讨论政治,无法说明我们上述的政治在“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步生成自己的规定性这一理论见解。所以,这种理路,看来看去,还是一种传播学,而不是政治传播理论。
二、社会中政治始终统摄着传播
传播是一种交流,交流是一种过程,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在这里,实际上“信息”是传播的核心,比“流动的过程”更为重要。至少说二者同等重要。但传播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这种信息,即把这种信息当作一种既定的东西,认为传播的变化就是传播过程的发展,认为传播学就是研究这种过程之规律的学问。
毫无疑问,传播的“过程”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越来越复杂,但是,传播学的研究者们把这种过程“研究”得更加复杂。打开现在任何一本传播学,浓墨描写的是过程,诸如线性的、非线性的、单向的、双向的、立体的、直接的、反馈的、系统的;还有所谓拉斯韦尔模式、神农一韦弗数学模式、奥斯古德模式、韦斯特利一麦克莱思模式、德弗勒反馈模式、赖利夫妇模式、马莱茨克模式、鲍尔一罗克希依赖模式等等,纷繁复杂,眼花缭乱!说实在的,不仅仅是非传播学研究者们很难理解和消化,即使是有些研究传播的学者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和消化。
为了使问题回归简单朴素,我们也就不古今中外地往前追索了,就让我们回到“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当年对传播的认识和研究上来。如前所述,施拉姆确认传播的“人类社会特质”的基本思想后,认为传播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他虽然之后对“传播关系”、“传播行为”、“传播契约”、“传播过程”等展开不断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与他对“信息”的认知是同一的。就是说,传播过程的展开与被传播之“信息”的生成扩展相互依托,是同一个过程。这一点,被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忽略了,注意力都放在了对传播过程的研究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传播学,只看到传播形式而看不到传播内容的原因。
事实上,施拉姆当年创建“传播学”时,首先研究了传播的内容——“信息”。在他的《传播学概论》里,专门有一节谈“信息的性质”。他指出“信息是传播的材料”,那么,“信息究竟指什么呢”?他借用香农和韦纳的思想,认为“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都叫做信息”。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施拉姆接着所讲的大量的通过信息流动“减少不确定性”而形成“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信息的“社会性内涵”的生成与展示过程。换句话说,我们是要通过人的社会性本质的生成与展示过程,才能知悉“传播”究竟在传什么!这也是“传播”必须由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来说明的原因。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