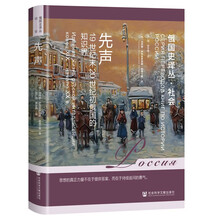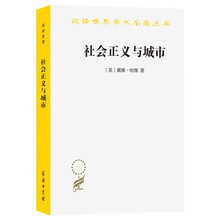《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
在莫斯论述文明时,欧洲有过不同的“文明”概念,“文明”被当成不同的东西,如市民化与国家化、礼仪与礼貌、艺术品味、世界崛起的手段等等。在语言学界,学者继承了西方古代观念,用“文明”来形容欧洲“语言文明”(如拉丁语、英语、德语等),并将之区别于土语、方言、未开化民族的少数语言、农村语言等“没有被广泛传播而因此不文雅的语言”。在国族时代,“文明”被视作“文化”——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莫斯对诸种“普通的文明观”加以区分,认为那些与传播相关的礼仪、品味、世界观、“语言文明”,都含有他自己定义的文明的要素,而国族时代忽略他人的文明的民族主义文明论,则与他自己的观点格格不入。莫斯将民族主义的文明论(以“文化”概念为特征)视为一种神话和集体表象,同时他也指出,在近代欧洲,还存在过一种普遍主义的文明论,这种文明论与视“文明”为一个完美的国家,一种封闭的、自治的、自给自足的状态的观点不同,它有世界主义的特征,却时常与抽象的、未来主义的文明论结合,成为对国族进行世界性的等级排序的手段,成为一种世界历史使命的信仰。如何在国族主义与普遍主义的文明论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状态?莫斯的答案似乎是“国际化”。“国际化”的文明既不同于民族主义,又不同于普遍主义,它既是“超社会的”,又与无限的、惟一文明有别。
20世纪初,随着人类学的“人文思想革命”的来临,为了寻找西方的“他者”,多数人类学家忙于寻找世界上尚存的“原始人”。19世纪的人类学家中广泛存在着对“原始人”与介于他们和近代文明之间的诸文明体系的关注。到20世纪,这个关注若不能说已全然消失,大部分也都不复存在了。莫斯一向尊重英、美人类学家书写的“原始人”民族志,且试图基于对它们的比较和综合而提出理论。然而,他也偏爱古代文明体系的研究。莫斯受过的民族学及印欧古代语文的训练,部分解释了他对于古代文明体系研究的偏爱;但更重要的是,对于“文明现象”的长期关注,使他远比其他人类学家更注重理解作为社会演化中间状态的古代文明体系。在莫斯看来,这些处在中间状态的文明,广泛存在着传播、帝国及复合,其历史,本身是“超社会体系”的极佳说明。
为了理解既不同于“社会”又不同于“世界”的文明形态,莫斯基于他的同僚与学生的研究,概述了古代诸文明的特征:
其一,从古希腊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看,文明都远距离地传播过物质和思想,并且涵盖除了文明主体民族之外的民族。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