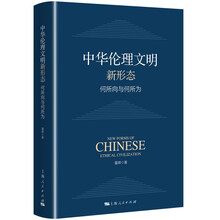“我”一开始就不是自我,而是在“顽念”中进入被动性的经验,并且承担不可推诿的责任。不仅仅如此,要彻底保持这个间接性的法则,还必须超越面容,思考爱欲以及生命的繁衍能产性等现象,这样身体的接触就转换为接触的不可能。通过抚摸的动作,女性的它异性才打开了身体之间的关系。
而对于德里达和南希而言,如果肯定胡塞尔的现象学原则,是不可能有着直接可通达性的。现象学本身就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并且应该承认这个不可能性,由此反而可以打开不同于胡塞尔现象学的道路。如果非现象学地思考身体,不仅仅是我能与自身感发的内在性与它异感发的超越性,而且是从身体的触觉或者触感出发,就发现其实并没有一个现存的身体本身,一方面是意识活动都建立在身体的触觉上一一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对触觉到触感的思考一没有什么心身二元论;另一方面,从身体触觉重新思考身体的关系,需要新的范畴,新的理论出发点,这是从延异出发的身体之为间隔,以及身体之为假器,并没有专门特有的触觉与对世界的认同。身体作为机器装置的前提条件下,身体以及相应的意识活动才可能被重新思考,避免传统形而上学对身体的贬低。这样的话,身体恰好需要中介,完全是非直接给予的,这就彻底打破了现象学的原则以及诸多内在性的建构。当然,德里达已经受到了莱维纳斯对不可看、不可触知的他者面容以及超越的发现的影响。
虽然在柏拉图那里,身体处于洞穴的位置,是要从中超越出来的,身体是灵魂的囚笼或者坟墓,但是在对爱欲的哲学的追问活动中,身体还是得到了某种亚里士多德《诗学》之悲剧式的净化。而基督教神学一方面处于不可见的上帝道成肉身的可见可触之中,另一方面,又在禁欲与苦行之中否定肉体。但真正的心身二元论,彻底对身体进行对象化处理,使之成为一个现存的自然物以及机械的对象,却是近代自然科学以及主体观的产物。
在胡塞尔看来,尤其在他晚期《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论的现象学》一书中,通过彻底地先验还原,回到主体性立场,清理了笛卡尔以来的心身二元论传统。这个二元论肇始于伽利略的物理学,它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对自然进行数学化,相信自然就其自在存在而言就是数学的。为了获得精确性,只有能够被几何学或者数学公式化的对象,并且体现出因果律的事件才具有真理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