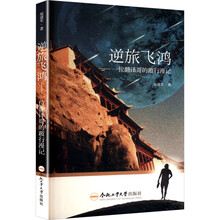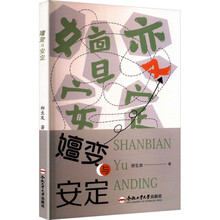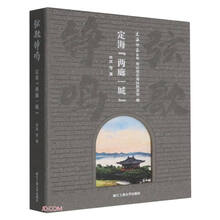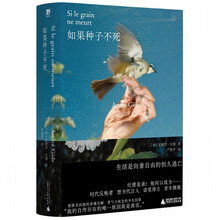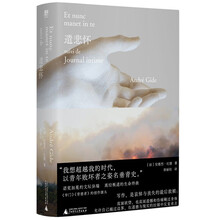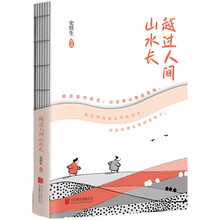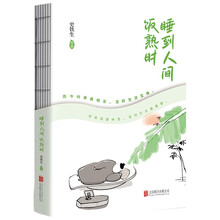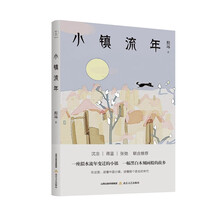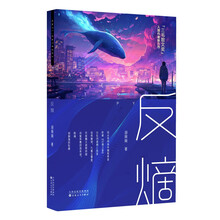仰望古城墙<br> 许崇乐<br> 是乍起的秋风撩拨着我怀古的幽思,还是潮州市区环城东路建筑物全面拆卸的消息触发了我的兴致,使我想看一看古城墙的容颜?这,可说不清楚。但我还是迎着深秋的风,踏着落日的剪影,来到了环城东路。一步步地走去,一次次地仰望。可惜,刚刚拆卸了的高低不同的建筑物,仍阻挡住我的视线。那灰黑色的、赤褐色的古城墙,只是一小片、一小角、一点点地显露出来。远远望去,这些古城墙像是一个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一套套古旧残破的衣衫、一双双目光灰暗的眼睛。我的心忍不住紧缩起来。我体验到一种被遗忘的忧伤。<br> 是的,是曾经被遗忘了。这长达2.3千米的古城墙,这现存的潮州古城最长的城墙,这标志着潮州古城正式形成的建筑物,这目睹潮州近千年历史变化的见证者,好长的时间被遗忘了。<br> 我不知道,公元1054年,太守郑伸动员民力全面维修内外城的时候,那个场面是否壮观;我也不知道,公元1370年,潮州指挥俞良辅组织民工把城墙向外移出的时候,能工巧匠是否众多。我只知道,建造城墙和维护城墙,除了军事上、水利上的目的和用途之外,还显示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近千年来,潮州古城东面这条城墙宛如一道屏障,抵御了外敌和洪水的侵袭;宛如一面巨镜,映照出时代的变迁;宛如一位神色凝重的巨人,默默地注视着人间万象。<br> 但如今已是公元2000年了。城堤达标整治工程已经动工。这位被密密匝匝的建筑物遮盖了很长时间的巨人,终于苏醒过来了。<br> 它睁开眼睛,看到被拆卸了的建筑物,看到了老朋友湘子桥,看到了旧相识笔架山,看到了秋天黄昏中轻快跳荡的韩江水,心底里该是一番什么样的滋味?<br> 我仰视着它,怀着对往昔潮州辉煌历史的敬重注视着它,却难以描述出它此刻心中的激动和欢乐。<br> 是的,当曾经被遗忘了的人,终于被人们所认识、所敬重的时候,总会感到异常的激动和欢乐。<br> 我登上东门楼旁的城堤,顺着城堤走去。<br> 在沉沉暮霭中,我俯视这忽隐忽现的古城墙,忽然想到朴素和庄重的魅力。古城墙的色彩并不绚丽,造型并不新颖,只有这样的灰黑色、赤褐色,只是这样高高地砌筑起来。但由于有深厚的历史内涵,有独特的无可代替的功能,它却引起我无尽的遐思和自豪的感情。朴素和庄重,是这位穿过历史风云、看过多少兴衰成败的巨人所具有的品性。俯视着它,也就是在阅读一部章节纷繁的历史书籍。<br> 这部历史书籍即将醒目地展示在世人面前。<br> 古城墙——屹立在环城东路上的巨人哟,也将以素朴和庄重,灿然呈现于人间。<br> 我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br> 难忘潮州石牌坊<br> 丁岗 陈放<br> 潮州牌坊街修复工程,目前已完成沿街建筑的整修设计和22座古牌坊的方案设计;众多海内外乡彦纷纷慷慨捐资助建。余生也晚,曾亲睹之府城牌坊虽只有“岳伯坊”、“省郎坊”、“忠节坊”等数座而已,对牌坊街的胜迹韵事却颇多留意,略有小得。<br> 坊,按《辞海》的解释,既指“市街村里的通称,如街坊,村坊”,又指“店铺”(如茶坊)、“工场”(如槽坊、染坊);牌坊,多用石建,旧时用以表扬忠孝节义或科第寿考等的建筑。牌坊一般以四立柱外加盖顶隔成三门三楼(或四楼)为其建筑形式,正如潮剧《苏六娘》中乳娘的一句台词所说的:“像厝,却没有房问;像墙,却开了那么多个门?”<br> 一提起牌坊,世人即联想起安徽歙县棠樾的牌坊群。该牌坊群坐落于歙县城西6千米处的棠樾村前,由7座巨型石牌坊组成,为建筑学界公认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古石牌坊群”。<br> 或许有人要质疑:地处粤东的潮州自古以来是历代州、郡、路、府的所在地,经济繁荣,人文鼎盛,明清两代累建的牌坊,其数量之多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仅城区就有石牌坊104座,位于太平路作南北向的有41座,东西向(在街巷口)的有15座,规模不是远远超过棠樾吗?为何桂冠旁落呢?请注意,“最大的……”前面还有一个限制词——“现存”!潮州太平路的石牌坊群,毕竟被拆卸已经50多年了(起因缘于1950年12月19日,太平路下水门街北侧“百岁乡宾坊”坠石砸死邮电工人而引发拆除全城石牌坊),当然未能得此殊荣,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留下的一个遗憾。<br> 现今拟修复的潮州牌坊街,位于太平路和东门街,路段总长1948米,修复的明清古牌坊22座(其中太平路20座,东门街2座):修复将以原址、原貌、原工艺为基本原则,尽可能利用古牌坊遗存的构件,力求恢复其真实风貌和艺术特色,并保护太平路和东门街传统商业街的历史风貌。功成之日,潮州牌坊街,将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最大的石牌坊街”。<br> 从现存图片及资料来看,太平路上古牌坊,都是四柱三门的形式,但是,一座一样,风采各异。坊额题字,或三字,或四字;书法风格,或遒劲,或雄浑;其安置在坊上的部位也不相同。<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