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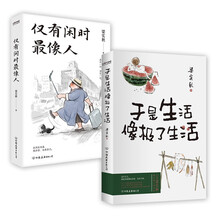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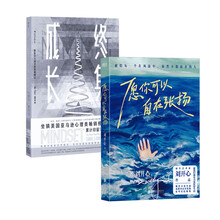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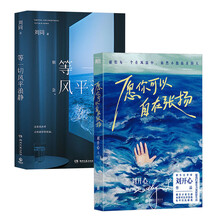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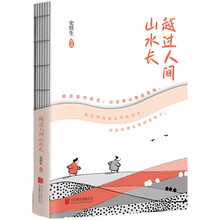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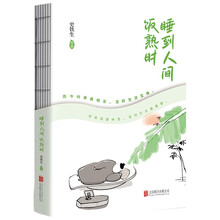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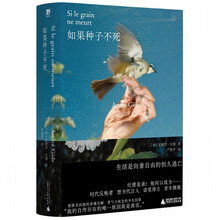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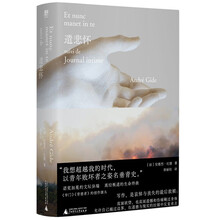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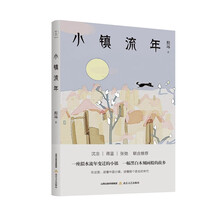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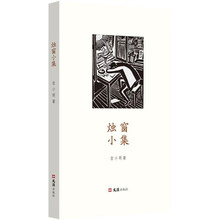
“一个可能很快就凋萎的桂冠,我一点都不想要。”
遭遇人生变故与舆论谴责之后,面对创作与道德间的冲撞与撕裂,
五十岁的纪德回望半生,展开近乎苛刻的自我清算,
写下坦率到天真的回忆录与忏悔书:
前半部分追溯敏感压抑的童年时光,悉数坦白青春的悸动与爱恋,
在他的成长路上,天性与束缚不断角力,禁欲主义与无畏之爱展开持久对峙。
后半部分记录改变纪德人生、写出《地粮》等系列作品的北非之旅及与王尔德等人的真实交往,
以率性之姿跃出时代的禁锢,引领数代青年展开一场朝向自由的长久叛逃。
“我是异端中的异端”
安德烈•纪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及领奖辞
1947年,安德烈·纪德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表彰其内容广博且极具艺术质地的著作,以对真理无畏的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见,呈现了人类的种种问题与处境。
翻开安德烈·纪德横跨半个世纪的日记,第一页中,年仅二十岁的作者身处拉丁区一栋大楼的七层,为他所属的青年团体“象征派”寻找集会地点。他望向窗外,看到塞纳河与巴黎圣母院沐浴在秋日黄昏的余晖之中,不禁感到自己就像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主人公拉斯蒂涅一样,正准备征服脚下这座城市:“现在,就看咱俩的了!”不过,纪德豪情万丈地踏上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前行之路,从不曾满足于轻易得来的胜利。
今天,这位七十八岁的作家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始终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职业生涯伊始,纪德率先成为精神危机的代言人,如今,他已然跻身法国最知名的文学家之列,其作品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跨越世代。他最早的作品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问世,最近一部作品则于一九四七年春季发表。他的作品清晰地勾勒出欧洲精神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也为他漫长的一生奠定了某种戏剧性的底色。也许有人会问,为何其作品的重要性直到最近才被广泛承认——安德烈·纪德无疑属于这样一类作家,对他们的充分认知需要长远的视角和能够容纳事物辩证发展的三段论结构的充足空间。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纪德的自我中含有许多彼此对立的成分,他是名副其实的普洛透斯,形体变化万千,天性中的两极不知疲倦地碰撞,激发出耀眼的火花。因此,他的作品以一种持续不断的对话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中,信仰与怀疑交锋,禁欲主义与无畏的爱对峙,约束与自由相互角力。甚至,他的生活本身也是流动而多变的;他于一九二七年前往刚果,一九三五年前往苏联——仅举这两个知名的例子,就足以证明他并非安于一隅的文人。
纪德出身于新教家庭,后者赋予他的社会地位使他能够自由地探索自己的使命,并比多数人更有条件专注于个性的培养和内在精神的发展。他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的著名回忆录作品中描述了自己的成长环境,书名《如果种子不死》典出《约翰福音》,代表种子在结出果实之前必须死去。尽管他曾对自己接受的清教徒教育做出强烈的反抗,但他一生不遗余力探讨的,皆为道德与宗教的根本问题,并且在某些时刻,以罕见的纯粹性阐释了基督之爱的讯息,尤其是一九○九年出版的小说《窄门》——这部作品足与拉辛的悲剧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在安德烈·纪德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明显的 “背德主义” 的踪迹——这一概念常常被他的批评者曲解。实际上,它指的是自由的行为,“无动机”的行为,抛弃一切束缚、摆脱一切成规的行为,正如美国隐士梭罗所言,“最糟糕的便是贩卖灵魂”。我们应当牢记,纪德将某种与公序良俗相悖的行为定义为美德,曾面临相当的阻力。一八九七年出版的《地粮》是他早年的一次尝试,后来,他的立场有所转变,而他热情歌咏的种种欢愉则让人联想到南方土地上美味多汁却不耐贮藏的果实。他对读者和追随他的青年所发出的号召——“现在,扔掉我的书吧,离开我!”——由他自己率先在之后的作品中践行。然而,在《地粮》及其他作品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仍然是他在散文的悠扬笛音中巧妙捕捉到的分离和回归的极致诗意。我们一次次重新发现着这种诗意,例如,在五月的一个清晨,他在布鲁萨的一座清真寺附近写下一篇简短的日记:“啊!重新开始,不断再来!如痴如醉地感受这细胞间的细腻柔和,情感似乳汁般渗透……繁茂花园中的灌木,纯洁的玫瑰,梧桐树荫下慵懒的花蕾,难道你从不曾见证我的青春?从前?我身处其中的,究竟是回忆吗?坐在清真寺的一隅、呼吸着、爱着你的,真的是我吗?抑或我只是在梦中爱着你?……如果我是真实的,这只燕子会离我这么近吗?”
在纪德的小说、散文、游记和时评文章中,在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的奇特且不断变化的视角背后,我们总能发现同样轻盈的智慧、同样纯粹透亮的心灵,而承载它们的语言以最审慎的手法呈现出了最古典的澄澈,捕捉到了最微妙的变化。在此,我们无法深入讨论全部作品,只提著名的《伪币制造者》,这部发表于一九二六年的作品对一群法国青年进行了大胆深刻的剖析,以其新颖的创作手法,开辟了当代叙事艺术的全新方向。前文提及的回忆录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纪德在书中以令人震动的诚实叙述自己的一生,不增添任何对自己有利的内容,也不隐藏任何令人不快的内容。卢梭曾怀抱同样的目标,但不同的是,卢梭展示了自身的缺点,只因他深信所有人都像他一样邪恶,无人敢对他进行评判或谴责。纪德则干脆拒绝给予世人评判他的权利;他呼喊着更高的审判庭,更广阔的视野,让他在至高无上的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因此,《圣经》中关于麦粒的神秘引文正蕴含着这部回忆录的深意,麦粒象征着人格:只要是有感知力的、深思熟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都只能孤独地栖息,无法发芽;唯有接受死亡和嬗变的代价,才能获得新的生命,结出果实。纪德写道:“我不认为有哪一种看待道德和宗教问题的方式,或面对这些问题时的行为方式,是我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不曾体验并据为己有的。事实上,我希望将所有的分歧加以调和,通过包容一切,将酒神狄俄尼索斯与太阳神阿波罗之间的争斗,交由基督来裁决。”
这段声明揭示了纪德在思想上的多面性;他常常因此受到指责和误解,但从未因此背叛自己。他的哲学倾向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新生,不禁让人联想到凤凰涅槃的奇迹。
今时今日,我们满怀敬仰之情,流连于纪德作品中丰富的思想和重要的主题,自然而然地忽略了作者本人似乎乐于激发的、具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即使到了晚年,他也从未主张完全、彻底地接纳过去的经历,或是得出确凿的结论。他最希望引发争论、提出质疑。纪德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或许不会体现在对其作品的全然接受上,而更可能在围绕其作品的激烈争论中显形。他真正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
借由几乎无与伦比的大胆剖白,纪德的书写即为一场反叛。他希望与法利赛人斗争,但在缠斗中很难避免触犯某些人性中相对微妙的准则。我们应当牢记,这样的行动是一种对真理的热切追求,而蒙田和卢梭之后,对真理的热爱便成了法国文学的公理。纪德从来都是文学完整性的真正捍卫者,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他坚信个体有权利,也有义务果敢而诚实地呈现内心的一切困惑。从这一角度来看,他漫长且丰富的创作活动,被各种方式所激励,蕴蓄着理想主义的价值。
安德烈·纪德先生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到场,他对这一殊荣深表感激,他的奖项现在将交给法国大使阁下。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晚宴上,由于诺贝尔奖得主安德烈·纪德无法出席,其获奖致辞由法国大使加布里埃尔·皮奥代为宣读。
我既无法见证这个庄严的时刻,也无法用自己的声音表达感激之情。我不得不放弃一次注定愉快而富有教益的旅程,就不在此赘述我的遗憾之情了。
众所周知,我一向拒绝接受荣誉,至少是那些国家授予法国人民的荣誉。诸位,我必须承认,我怀着一种眩晕的心情接受了您们授予我的奖项—— 一位作家所能收获的至高殊荣。 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荒野中高声疾呼,后来又以为自己仅仅在对极少数人讲话,但今天,您们向我证明,少数人的力量值得信赖,微末之焰也能燃尽荒原。
先生们,在我看来,评委会的选票与其说是投给我的作品,不如说是投给推动我创作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的时代正遭受来自各方的攻击。您们不仅承认了这种精神,而且认为有必要保护和捍卫这种精神,这使我充满信心,内心被赋予了极大的满足。然而,我不禁想到,直到最近,法国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能代表这种精神。我指的是保罗·瓦莱里,在与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中,我对他的钦佩之情与日俱增。仅仅因为他已不在人世,否则今天站在这里接受表彰的应该是他。我常常说,我一直怀着多么友善的敬意,毫无保留地被他的天资折服。在他面前,我总觉得自己只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但愿对他的缅怀能够成为这场典礼的一部分,在我看来,随着周遭的黑暗愈加浓厚,他所代表的精神也愈发光彩夺目。您们今日为自由的精神加冕,并在这个暂时消除派系分歧、消弭一切边界的授奖时刻,为这种精神提供了罕见的光芒万丈的舞台。
“我是异端中的异端”安德烈·纪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及领奖辞..........i
如果种子不死........................................................1
第一部..............................................................3
第二部.............................................................369
附录...............................................................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