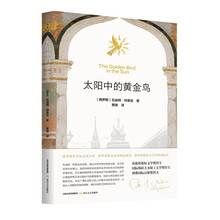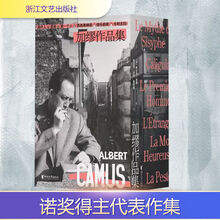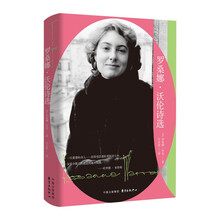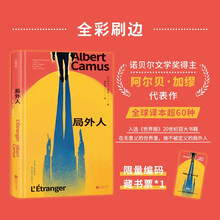我父亲的额叶——因中风于2009年
6月24日不安详地死在了加州圣
地亚哥的斯克里普斯纪念医院里。
1940年1月20日出生的额叶走过
了美好的一生。额叶喜欢当大哥,
它想再说说话,可有人给它套上了
袋子。额叶死的时候咬住了自己的
嘴唇,就像拉紧了一扇窗户。父亲
在他话语的葬礼上却不停地要说
话,他的爱穿过我的身体落在了并
不存在的地面上。我听到有人在跺
脚。身体和语言一样令人困惑:额
叶是在发脾气还是在跳舞呢?我拿
走了父亲的手机,他的话语在塑料
棺材里死去了。在他话语的葬礼上,
我们为我的流产争论不休。他说:
“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婴儿。”我无
话可说,跺着脚冲出门去摇醒那个
死婴。我想到了那个放下魔棒的急
救员,她在摸不到心跳的时候悄悄
地离开了房间。那时我终于明白了,
黑暗在无止境地坠落,黑暗并没有
吸入所有的色彩,而是吞下了所有
的语言。
我的母亲——因肺纤维化于2015年
8月3日不安详地死在了加州阿纳
海姆核桃村养老院她自己的房间里。
她的房间是在2012年7月3日出生
的。这个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
子。也没有核桃树。只有切花。安
宁疗护的护士默默地把听诊器放在
母亲肺部的上方,等待它扩张。等待
成了一种伤害。就像护士深吸一口
气、闭上眼睛、呼出一口气说“对
不起”的样子。血液是涌到了我的
脸上还是指尖?护士说“对不起”
之前或之后有没有再睁开眼睛?回
忆是枪响之后的鸣响。我们试着回
忆枪响却记不起来。就像是回忆在
人死后站了起来,迈开了步子。
张明皚——于2009年6月24日在
不知不觉中死在了I-405号高速公路
上。她出生在汽车城,死在高速公
路上也算死得其所。母亲来电告诉
她父亲心脏病发作时,她的生活有
了凹陷,她像不再汲水的燕子。这
不是她第一次死亡。除了这次,她
所有的死亡都带着褶皱。母亲的误
判(其实是中风)并不重要,要紧
的是张明皚得问要不要她开车去
看额叶。母亲说“要”时,张明皚感
觉自己并不想去。有人听到了这种感
觉。因为父亲没有死,但失去了话
语。在医院,她哭了,她再也听不
懂父亲说的话了。之前,她并不理
解父亲的病情有多残酷。这是她最
后一次在这种疾病面前哭泣。她和
自己的影子交换了位置,因为痛苦
会改变形状,因为痛苦会偷偷发生。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