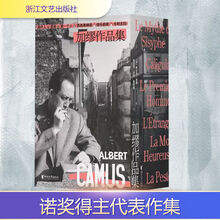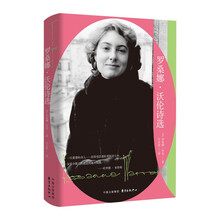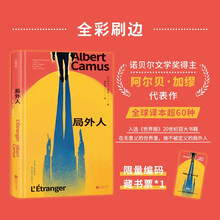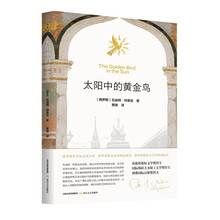起跑线
跑步时,我通常会闭上双眼。闭上双眼是为了专注于奔跑的感觉,否则我可能会失去它,那种双脚“咚——咚——咚”敲击地面的感觉。在接近最高速度时,我感觉双腿从身下脱离,整个人开始飘浮在空中。所以,我必须闭上眼睛,集中注意力,确保自己不会飘走。这就是我保持脚踏实地的方法。我把世界上所有其他事物——我周围的一切——全都屏蔽掉,这样我就不会因为分心而忘了自己的节奏。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在巴哈马,人们总说,我无论去哪儿都会跑着去。
“甜豆儿。”妈妈那时会说——她总是那么叫我,“甜豆儿,我需要你跑步去一趟商店,听清楚我在这里跟你说的每句话。”
当我还是个女孩时,我总是在院子里或者大街上玩耍。我们租了一间有粉色墙壁和白色装饰线条的木板房,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房子很简陋,家具也很少,但是非常干净。我们用井里打上来的水洗衣服,把老旧的木地板擦得锃亮——妈妈想要在地板上照见她的脸,所以我们会把椰子切成两半,放在前廊上晾上几个小时,直到它变得十分毛糙,跟刷子一样,以便用来擦地板。
妈妈过去常说:“当你穷的时候,有很多事儿你都需要知道。”
换句话说,你要想办法利用好手头的东西来过日子。所以我会用椰子壳去擦地板,把地板擦得锃亮。
当椰子树的树枝掉下来时,我们会把它们收集起来打扫房子;水槽里不允许留盘子,绝对不允许。你必须收拾干净并保持整洁。所以,作为一个女孩,我总觉得——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和我一样——妈妈认为她必须教我明白某些事儿。
我们买不起太多东西,但妈妈记得有一个圣诞节的早晨,她给了我一个洋娃娃。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掉它的头,然后卸下它的胳膊和两条腿,只拿着肚子玩。
“波琳,你得把娃娃的腿安回去。”妈妈说。
“不,妈妈,我长大了要当一名外科医生。我需要学习如何做手术。”
听到我的回答,妈妈甚至都没笑一一她大吃一惊:她的女儿(家里六个孩子中的一个),还这么小,竟然在贫民窟里做着当外科医生的梦!
“好吧,我会一直帮你。”妈妈记得她当时这么说,“我会尽我所能让你读完大学,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名医生。”
在我家,家规和教育是最重要的。妈妈在这两件事上绝不含糊。
我只能想象她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当时,那个圣诞节,送她的女儿上大学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好比送我上月球一样。但在我小的时候,我从未感觉到梦想被打压。爸爸妈妈从未让我觉得我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让我去梦想。
“甜豆儿!”她又喊道。我从不让她等太久。
我马上从忙果树上跳下来,K快地跑到她身边。
我的妈妈,梅尔·戴维斯·杜桑(Merle Davis Toussaint),是一位美丽的女性。她来自牙买加,有着一头深色长发,深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深棕色的皮肤略带金色光泽。
她的祖母,我的曾外祖母,来自印度,是19世纪末从印度次大陆移民到牙买加的庞大群体中的一员。我母亲身上一半的印度血统让她看起来不同寻常,充满异国情调,我想我大概也继承了这一点。成年以后,我依然记得在机场被陌生人拦住的经历。
人们会问:“你有印度血统,对吗?”
每当这种事情发生时,我总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毕竟,我根本不认识问我的这些人。但这总让我意识到,我身上流淌着丰富的文化血脉。
我的外祖母在妈妈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从那时起,妈妈的姨妈就一直照顾着她,并最终把她带到了巴哈马,开始了新的生活。从那以后,妈妈的生活永远地改变了。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生活也是如此。
梅尔·戴维斯·杜桑站在我们的小木屋前,手里拿着几美元、两个草篮子,但没有购物清单。她会把所有要买的东西说出来——我必须当场记住。
“我往地上吐口唾沫。”妈妈那时常说,“在那口唾沫干之前,你要带着我刚刚让你买的所有东西回来。”
“好的,妈妈。”我会恭敬地回应,并伸手接过钱。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