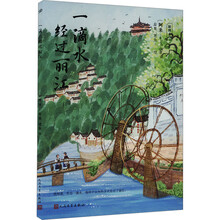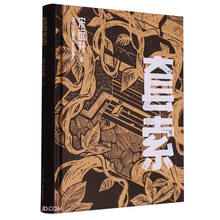父亲和牛
鸡啼头遍,父亲就起来了。清澈的月光像流水一样泻下来,把地面照得仿如白昼。土狗子叫得正欢。父亲到灶房烧了一壶水,火光映着他的脸,他脸上按捺不住的激动跟随着火光在跳跃。水烧好后,父亲匆匆刷了一把脸,随手扣上一顶草帽就出了门。
父亲要赶到三十多里外的六舅家。六舅日前托人捎了话过来,说牛犊子已满月,可去牵回。六舅的话,还滚烫着,让父亲整晚没有一刻睡得踏实。
早在半年前,六舅家的母牛肚子刚鼓起来时,父亲就和六舅商定好了,等牛犊子生下来,满月就让父亲牵去。父亲迫切需要一头牛。犁田、耙田、拉车,牛都是最好把式。人的力气再大,也没有牛的力气大。阿公那时刚给父亲分了家,除去几亩薄田,还有一身债务。要想日子红火起来,得养一头牛。
日上三竿时,父亲就到了六舅家。六舅刚割牛草回来,见到父亲,还是愣了一下。六舅没承想父亲行动这般迅速,他以为父亲的动作再快,也是几天后的事情。六舅要留父亲吃早饭。父亲说,不了,不耽误事了。说完,拉着六舅到一旁角落交割清楚,然后给牛犊子套上牛笼头,就脚踏着火轮返程了。
父亲把牛犊子当成了他的儿子一般。每天天还没有亮,父亲就出门去割牛草。割回来的牛草,还沾着晶莹的露珠。父亲在晒谷场铺上麻袋,细心地把牛草一棵棵摊开,让太阳把露珠赶跑。父亲绝不会让他的牛犊子吃到沾有露珠的牛草,那样牛犊子会拉稀,几天的牛草就白割了。在太阳落山前,父亲还会顺手搭回一担子牛草,夜里给牛犊子添上三两回。牛犊子的肚子永远是圆滚的,没有一时半会瘪下去。父亲懂得“马无夜草不肥”的道理。
太阳滚烫的中午,时常可看到父亲将牛犊子牵到小溪边的树荫下,双手一掬掬捧水给牛犊子浇水降温。水滴沿着牛犊子的肚皮滑落下来,再次汇入小溪。牛犊子欢畅地甩着尾巴,甩给父亲满身水珠,父亲却一点儿也不恼。
牛犊子像雨后的春笋“嗖嗖”地长开来。才三个多月的功夫,就已经长到了一百多斤。母亲到圩上买回了新牛绳和鼻环,让父亲给牛犊子穿鼻子。母亲把牛犊子的头按在一棵树旁,用碘酒给牛鼻子消过毒,然后抓住牛犊子刚冒出来的两只犄角。父亲拿穿孔器的手在颤抖,母亲多次催促,他仍下不去手,气得母亲骂他是个大草包。父亲将穿孔器塞到母亲手里,抹着眼泪往屋里走。他看不得牛犊子的鼻子被锋利的穿孔器刺穿。那天,母亲一个人完成了牛犊子的穿鼻之礼。之后好几天,母亲都不和父亲说话。
……
探亲
霜降过后,芝麻墨绿的枝叶在一夜之间黯淡下来,被迫裸露的豆荚迫不及待地咧开嘴,无数黑乎乎的小脑袋探出半个身子,好奇地打量着被白霜淹没的萧瑟的田野。
爹无疑是激动着的。那块巴掌大的地,居然打了整整一担子芝麻。黑油油的芝麻,把爹的心压得熨帖实实的。
这块地,曾荒芜了好些年头。每次路过,爹都可惜得牙齿直打颤。这地肥沃着哩,把土块捏在手里,稍微用力就能捏出黑油来。爹早就觊觎上了这块地。爹的眼光曾长久地落在这块地上,嘴里不止地念叨,这块地要是交给俺来耕种,那该多中啊!
果真事遂人愿。爹没有想到的是,一块大大的馅饼砸在了自个儿头上。分田到户时,这块地居然分到了爹手里。那一夜,爹没有一时半会睡踏实。哪怕挤不出两滴尿液,他也会搪塞娘,说要起夜去。那天夜里,爹的头靠在田畦,抽了整夜的旱烟,流了整夜的热泪。
收割过后,爹把芝麻秆收拢了起来,扎成捆,堆在柴房。爹舍不得用芝麻秆来烧火。爹懂得,芝麻秆大有用处,得留着。爹留着芝麻秆在寒冬腊月时用来喂牛。爹省吃俭用买了一头牛仔。爹知道,人的力气再大,也没有牛的力气大。日子要过得红火,得养一头牛。
黑油油的芝麻差点儿就亮瞎了爹的眼睛。爹仿佛想起了什么一般,用力一拍大腿,斩钉截铁地对娘说,差点儿坏了事,吃水不忘挖井人,咱得给大恩人送点儿芝麻。
听说爹要送芝麻到北京,俺二爹凑上来,问爹能不能缓几天再出发?二爹养了一头大肥猪,本想留到腊月再杀做熏肉,但听说爹要到北京去见大恩人,二爹想也没想就把猪给杀了。二爹想让大恩人尝尝他做的熏肉。二爹做的熏肉是当地一绝。二爹自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二爹说,要不是大恩人,俺再厉害,也养不了一头大肥猪。爹想,二爹说得着实在理。
爹一贯行事低调,想悄悄地去,悄悄地回,不想太多人知道这事儿。但二爹嘴大,到处嚷嚷,说爹要到北京答谢大恩人。不大会功夫,俺家就聚满了人,东家送来在山上摘的野菌,西家拿来河里刚捞上来的鲜鱼,张家李家说什么也要表示表示。爹装了满满当当一担子。后来者担子装不下,又是懊恼,又是抱怨,说爹不买他的面子。
爹狠狠地给了二爹屁股一脚,俺就说吧,这事儿办得……办得不大妥当!
不妥当归不妥当,爹出门时,俺看见他的神情,着实欢喜得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