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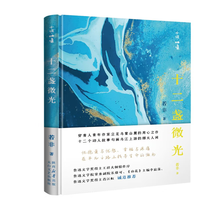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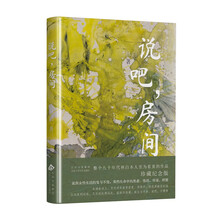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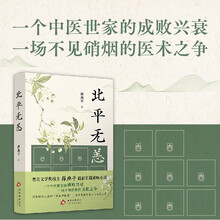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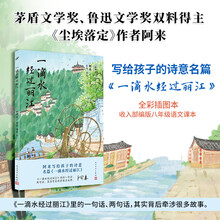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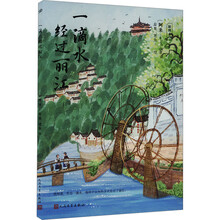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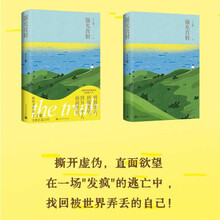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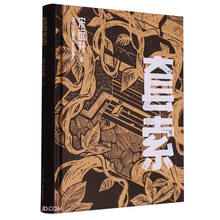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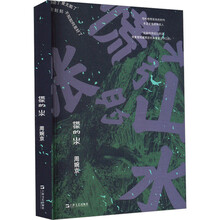


是什么让一群老人毅然离家出走,齐聚一座神秘的老人院?
是什么让一位九旬老人卷入命案,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
又是什么,让高龄被告选择沉默,拒绝辩护,甘愿背负命运的终审判决?
当“长寿”成为常态,我们是否真正准备好面对变老的现实?
在快速老龄化的社会中,如何守护每一个人晚年的尊严与选择?
当法律、伦理与生命尊严交织,我们是否真的理解“衰老”意味着什么?
在这部关于老年、命运与人性抉择的深刻小说中,旅日华人女作家陈永和借一桩“九旬老人涉嫌杀人案”,揭开了隐藏在制度与家庭之间、静默而激烈的代际冲突与生死议题。
1.不仅是一桩案件的调查,更是一场关于老年生活、尊严与主动权的深刻讨论:临近退休的律师林抵达接手了这起罕见的高龄犯罪案件,在抽丝剥茧的调查中,他不仅靠近了真相,也不得不面对自己作为中年人、作为“下一位老人”的深层焦虑与觉醒。
2.陈永和,一位生活于福州与北海道之间的华人女性作家,以她独特的跨文化视角和性别经验,细腻呈现出老龄社会的深层裂痕:小说中既有对死亡议题的哲学思辨,也有对养老制度、家庭结构与女性命运的深度洞察。
3.《收获长篇小说2024夏卷》倾情首发。正如评论家行超所言:“陈永和写出了人们面对生死时的观念差异,也写出了个体意愿与集体安排(家庭、家族、国家)之间的激烈张力。她用小说回应了当下中国社会越来越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如何面对老去?”
临近退休的律师林抵达接手了最后一次辩护工作,被辩护人是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他杀死了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但犯人内心却拒绝律师辩护。法庭上他既认罪又不认罪,但因为犯人昏倒,法庭终止了审判。在抢救他时,人们发现他衣服上写着“不要抢救我”几个字。围绕着案件的性质和要不要抢救近似植物人的犯人,林律师展开了调查……从传统伦理到个人选择,小说从不同方面多层次地展现了人生最后一关的复杂性——它静默如谜。
第一部
一
林律师的门牙掉了。
二○一七年的一个清晨,林律师独自在家用早餐——吐司咖啡加鸡蛋,突然听到咯噔一声,一看,是门牙掉了, 嘴一张,一排白牙正中露出个黑洞,看上去怪怪的。 这就麻烦了,上午十点钟,他要出庭辩护。
本来缺了一颗门牙,在法庭上说话漏风,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林律师的自我感觉坏极了,今天有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出庭,一年多前,他就已经不接手新案子,这次完全是看在老朋友刑警的面上。更关键的是,在潜意识中,他认为,人性的完美中不能缺少门牙,就像人不能不穿衣服,这是个原则问题。
有原则的人在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离开了秩序这个世界就要分崩离析。
林律师本来打算在开庭前再研究一下案子卷宗,但心绪烦乱,做不到了,这也让他懊恼,完美人格怎么能受门牙影响呢?
直到开庭前十分钟,他才回过神来,打开卷宗,匆匆翻了一遍。
这是个让林律师感兴趣的案子,最早跟刑警闲聊中听到的,一个九十岁老人杀死了一个八十六岁老人。
刑警当笑话说给林律师听。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案件总被当下酒菜来谈。
林律师一听,兴头就来了,瞬间把自己碰过的案件在头脑里过了一遍,意识到,到目前为止,他处理的案件中,罪犯年纪最大的不超过七十岁。
一桩很确定的杀人案,不存在任何疑点。刑警说,被告A在行凶现场被警察逮捕,被指控为故意杀人罪。作案地点在距离C城车程大约二小时、偏僻深山桃花村的杯心老人院,发现时,被告A正用毛巾捂住被害者嘴巴,并抗拒警察高声呼叫停止的命令,拒不开门,继续行凶,直到被害死亡。
警察破门而入,当场逮捕了A。
被告A无任何反抗拘捕行为。被捕后,他除了供认犯罪行为外,对其他事一概保持沉默。
一个老人,你能对他怎么样?随时都可能躺倒在审讯室里。刑警说,更奇怪的是,他好像执意要上法庭,问什么都说上法庭说。
你抓了我,我就要上法庭。被告A对刑警说。所有有利的建议他都听不进去。
所以犯罪原因到现在还是一团谜。
警方已经查明死者叫林某某,家住某街道某巷某号,退休前在某大学任教,无后裔,退休后与老伴同住,十几年前老伴去世后一直独居。大约二○○六年春节前,居委会主任张大等人例行巡回慰问辖区内七十五岁以上老人,到林某某家,叫门无人应答,问左邻右舍,均说有一段时间未见其人。居委会主任张大感觉不对,找一人开锁后破门而入,发现屋内完好,无失窃现象,只是林某某不在其中。
林某某平日不出门,采购一类杂务委托一邻居代办。据邻居说,林某某每次除应付的购物款外都会多给她一点小费。林某某无亲无故,平日几无见人来访,所以张大认为他有失踪的可能。
张大表姐恰巧就是林某某的那个邻居,知道他失踪后,夜里做了个梦——林某某身体没了,只一个头瞪着大眼睛在黑暗中飘来飘去。她醒来很害怕,就怂恿张大去报警,于是张大就给公安局某处一熟悉的哥们挂了个电话。
当然,谁也不会在意一个七十五岁老人的失踪,这些年不是发生了许多老人失踪案吗?这种老人,谁要呢?躲都来不及。
……
第一部----------001
第二部----------131
第三部----------239
尾 声----------325
后 记----------335
对待死亡,作者陈永和真正主张的是放下,无论是对待他人还是对待自己,都应该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执念,将身体/生命的处置权交还给它本身,顺其自然、依势而为——这应该也是作家想要带给我们的死亡教育。
——行超(《文艺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