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教数学的老师,辽宁人,国民党时代的老牌大学生。“文革”时谁学数学呢?学生都不太听他的课,有时人都跑光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拉着我们说,年轻人一定要学东西,今后会有用,今后会有用。他真是想教我们,就几个人,他也一丝不苟地讲。现在这个老人在的话,应该有九十多岁了。
还有很多很多好老师,包括我的体育老师,两口子都姓陈,陈德威、陈启华,成都人。我在县里体操队干过,~成绩不行,但也是受两位陈老师的影响。他们说,你身材不错,就是不努力。
“文革”时,县二中也有“专政”对象,有两个我也去欺负过。
一位是姓王的右派,好像是副校长。造反当局决定将他遣返农村,他不愿意,坚守不走。造反派姓刘_的负责人找到我们六七个人,让我们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明确指示,整他,不要整凶了。
我们围住王校长,先是指责,进而推搡,最后出拳,算打人了。
我参加了抓扯,但心里还是有障碍,没有打王校长,但终是干了坏事。
还有一件错事是污辱一位叫杜宗美(音)的老师。
校园里这位低头缩脑的老师很引人注目,矮矮胖胖,光头,戴个黑框眼镜。他好像有海外关系,留过洋,好像还是北大毕业的,总之在“文革”时是个“坏分子”。我觉得他很反动,敢在名字中表示忠于美帝(美国,那时就叫美帝国主义,简称“美帝”)。我们叫,杜宗美,站好!他就站住。等我们命他滚蛋,他才退走。当时他可能已经有点精神病了,丧魂落魄,衣服是自己粗针大线缝的,无领无袋过膝,穿着单薄,大冬天赤脚,后来他变成孤魂野鬼了,住在一个狭窄的楼梯间里,除一席一碗一筷,再无长物。他白天不出晚上出,你发命令,他抗命了,冷目视你,让你无趣以至不自在。
再后来,他在校园里出现得越来越少。最后,听说他死了。
我上初中,十三岁,在形成人生观的时候,在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遇到了这批顶级老师,遇到了这些忧国忧民、见多识广、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我觉得真是幸运。现在很难遇到这样威风的师资队伍了。我上小学,遇到的是一般的比较敬业的老师,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小学没有被污染,但上中学的时候,我遇到了名师高人。
因为历史原因,他们被集中到柏溪镇,他们不可能去宜宾市的好学校,他们被放逐到一个很贫穷偏僻的学校,而正好我在那儿上学。
我真的觉得他们都是绝代风华,他们都很优秀,每个人都见多识广,每个人都气度非凡。他们这种气质,跟镇上的南下干部也好,农民也好,市民也好,完全格格不入,但是那几年他们还是生存下来了。
“文革”结束后,他们大多数纷纷高飞,离开了宜宾县二中;改革开放以后,都还有一个好的晚年。
我们班的同学百分之六十是农村的,这些老师看重我,可能觉得我不是农村孩子,觉得我跟这些农村孩子还是有一些区别,好像就是悟性高一点,谈得来一点。他们喜欢我,我跟随他们就紧一点。
他们真的让我比别的孩子想得远,什么宇宙啊,银河系啊,很膨胀。
他们聊天时我在一旁听,他们讲的一些想不通的事,也使我有许多困扰。比如说这样一个我多年想不通的问题:银河系作为一个参照,宇宙作为一个参照,怎么比喻?没法比喻嘛。如果银河系是一个灰尘,宇宙是什么呢?怎么去定位宇宙,是看到的天空吗?不对啊,那是有限的啊。像这种想法,就不断地困扰我,如果没有这些老师,就不会有这些困扰。因为想这些问题,觉得人特别渺小,也就想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就有所定位了。对文化大革命,有时他们也会发表一些见解,虽然是只言片语,但会不一样,跟社论报纸说的不一样,甚至还会说上海的一些小道消息。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还可以这样想,真是太牛了,太大胆了。
我觉得他们的影响是隐形的、潜移默化的。进了他们的房间,看到桌子上铺的方格子布,很洋气,他们穿的衣服,他们说话的语气,包括他们讲课的手势……后来我反思,觉得这段经历太重要了,他们的影响看起来只是点点滴滴,但对我一生都发生作用。它使我变得特别愿意和有智慧的人交往,而且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观念,保持和高人的交往,包括到成都后与马识途、车辐、流沙河、魏明伦、邓贤、朱成、何多苓、周春芽等人交往。一个人,人生路上去交有智慧的朋友,以思想换思想,以智慧换智慧,就会受益。所以,我中学时期遇到的这些老师,他们留给我的这种财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特别广泛的,无以言表的。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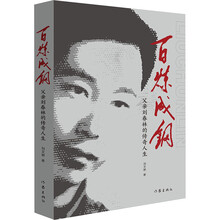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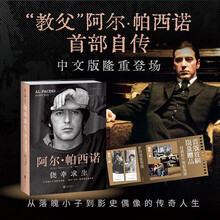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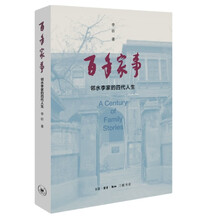



——曾彦修
看他办博物馆立志救世,“为人太多,自为太少”,很像庄子书中的尹文子。至于粗茶淡饭,布服素衣,“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又很像墨子。……吾国中原黄土深厚,蕴藏哲理,宜有儒道两家之外,墨家一脉精神延续下来,而见之于某人如建川者。
——流沙河
你有想法,有作为,我很敬佩你。你的工作很有意义,为中华民族留下记忆。
——连战
建川,你要是生在民国,你的造就肯定会更大,你肯定上战场,当将军。哎呀,不过你生在这个时代,也做了一件大事。
——陈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