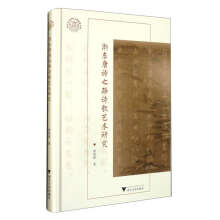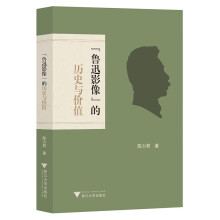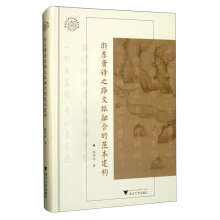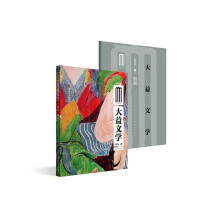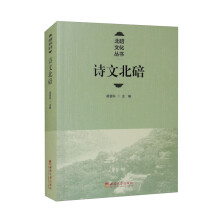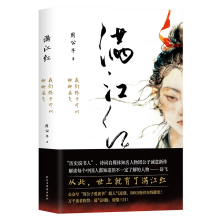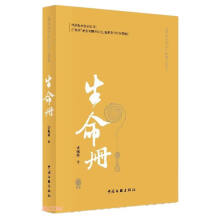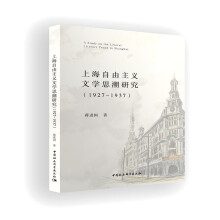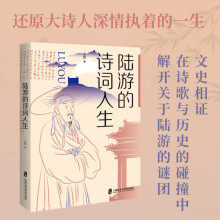《“《春秋》笔法”的修辞学研究》:
自孔子修订《春秋》以来,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等义例之探讨,代不乏人。如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颖容《春秋释例》,晋杜预《春秋释例》和《春秋经传集解》,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宋陈德宁《公羊新例》、刘敞《春秋传说例》、沈棐《春秋比事》二十卷,元黄泽《三传义例考》、赵汸《春秋属辞》十五卷,明傅逊《左传属事》二十卷、石光霁《春秋书法钩玄》、张溥《春秋三书》中有《春秋书法解》一卷,清刘曾璇《春秋书法比义》、徐经《春秋书法凡例》(附胡氏释例)、刘逢禄《公羊春秋何氏释例》、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记》、方苞《左传义法解要》和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
康有为之《春秋董氏学》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在近代以前,对所谓“《春秋》笔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春秋》基本义例的探讨上,很多著作是通过对《春秋》三传中文字的考证和义例的阐释去发掘《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并由此总结出相关的一些“书法”凡例。但是这种研究状况在19世纪末期随着传统经学的逐渐解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康有为把孔子塑造为“托古改制”的“素王”上,在康氏看来,《春秋》其实就是孑L子托古改制的著作,他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去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从而表达出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变法的政治理想。康有为把孔子塑造为“托古改制”的先师,从重新阐释孔子微言大义的角度出发,从而完成了经学向现实的逻辑转换,这些“微言大义”其实就是“《春秋》笔法”的具体内涵,经此一变,孔子的形象有了彻底的改变。康有为的“《春秋》笔法”研究主要体现在其著作《春秋董氏学》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传统的经学研究在经过清代的古文、今文等流派的整合和复兴之后,逐渐开始走向末路。在这一时期,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方面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民族和社会矛盾激化;另一方面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传统经学在“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冲击下埋头书斋不问世事的情况越来越呈现出自己的弊端,这样“经为今用”的问题就现实地摆到经学家的案头上来了。比如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其指向性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对“《春秋》笔法”的具体研究来探讨一条经世治国的道路,其实也是为经学的研究寻找出路。重新对儒家哲学进行阐释,力图来经世救国是康有为等今文学派突出的特点。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春秋例第二》中说:“学《春秋》者,不知讬古改制、五始、三世、内外、详略、已明不著、得端贯连、无通辞而从变、诡名实而避文,则《春秋》等于断烂朝报,不可读也。”
《春秋董氏学》最初由康氏弟子编于1896年,1897年由康广仁在上海同译书局刻印出版,其时正逢戊戌变法前夕。全书除“自序”之外,一共分为八卷,分别由《春秋恉第一》《春秋例第二》《春秋礼第三》《春秋口说第四》《春秋改制第五》《春秋微言大义第六(上、下)》《传经表第七》和《董子经说第八》组成。其中第1-6卷为康有为摘编董仲舒《春秋繁露》一书,突破从文字音韵进行训诂解经的范例,按照同类合并的原则分门别类摘编组合,并加上相关按语对此进行重新阐释,从而推导出新的结论。在这六卷中,《春秋恉第一》《春秋例第二》《春秋微言大义第六(上、下)》则可以说是对“《春秋》笔法”的具体性研究。比如《春秋恉第一》中“天子诸侯等杀”“立君书不书”“诛细恶以止乱”“战有恶有善”“讳大恶”“不畏强暴”则分别指向“《春秋》笔法”中的直书、惩恶劝善等书法原则;而《春秋例第二》中“五始”“时月”“王鲁”“内外”“贵贱”“屈伸详略”“微辞婉辞温辞”等则是对具体书法体例的探讨;《春秋微言大义第六(上、下)》则是对“《春秋》笔法”所体现的“大义”的抉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