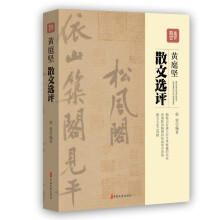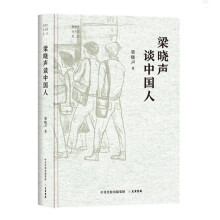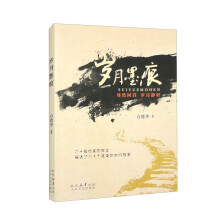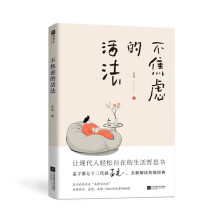拥吻的尴尬
巴西之所以老是给人造成热情的印象,拥吻的习惯可能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拥吻在巴西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是日常生活的常规项目,如果一个人有得几天没有拥吻或者没被拥吻,那只能说明,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他陷入了可怕的孤独,或者,他干脆就是被关在单身囚室的犯人。
欧美许多国家的人民都有在打招呼时接触身体的习惯,但他们要么象征性地像两条鱼在水中擦身而过一样轻碰脸颊,要么手臂相交小示兴奋,而且仅限于熟人之间。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像巴西人一样,就连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也要踏踏实实地拥个结实、吻个脆响,更不用说熟人和朋友之间了。
巴西人的拥吻一般是这样进行的:在初次见面被人引见之时,或者天天碰面的熟人每天第一次见面之时,如果双方是异性或者两个女性,就必须同时张开双臂扑向对方,死死把对方抱住,同时用嘴唇剧烈地摩擦对方的面部并努力咂嘴,发出尽可能巨大的声响,而后一方问曰“嘟嘟笨”(Todobem一切都好吗?),一方答曰“嘟嘟笨”(Todobem!都好都好!)。告别时亦是如此,不过不喊“嘟嘟笨”而喊“翘”(Chao,再见),跟大家都要“翘课”一样。据说在巴西各地,对于咂嘴的声响到底需要几声各有不同的规定,但到目前为止我对此还没有摸透,还得深入拥吻学习。
虽则拥吻看似很有“肉身性”,但对于巴西人来讲,这只是不动声色的客套而已,其间自有若干法度和界限不容僭越。譬如说,可以在脸颊上亲得咸湿无比,但不得用嘴接触对方的耳朵、下巴和鼻子,那是恋人的特区。也不能随便咸湿额头,那是老爸老妈专用的地盘。一个德国哥们跟我讲了他刚来时遇到的麻烦——他不知道热烈的拥吻其实也有禁忌,为了迎合扑过来的女同事,他胡乱在她脸上咂了几口,没想到乱中咂到了耳朵根,结果被愤怒的女同事抽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对于我来说,拥吻开始还比较新鲜,后来渐渐开始像负担一样觉得麻烦起来,尤其是去参加人数众多的Festa的时候,进进出出都得和人像中国的奸夫淫妇一样亲热一下,一晚上最多能重复上百次,感觉又累又别扭,毕竟,不是自己的礼仪。无休止的拥吻有时还会带来极度的尴尬,这里暂列数条与诸位倾诉:其一,虽则拥吻是异性之间或者两个女性之间的礼节,可是有些醉酒的男性也会对另一个男性施以拥吻。我有若干次在Festa上被胡子吧碴的醉汉哥们咂脸,险些导致我的性取向认同危机;其二,我最害怕和我的法国女邻居罗塞妮拥吻,她只要双臂一张,腋下汹涌的法国狐臭就会掀起惊涛骇浪,毫无保留地溺死我身上所有的热情细胞;其三,一件最最尴尬的事情。一次我在友人家游完泳后,去泳池边上的桑拿室小蒸,其间突然闯进两个身材绝佳的比基尼女。桑拿室本就狭促,可见的皆可见,此二女又偏偏被同蒸桑拿的另一个哥们引见给我认识。当二女分别扑过来贴身拥吻、大叫“嘟嘟笨”的时候,我却高呼一声“翘”逃出了桑拿室——因为我不合时宜地真的“翘”了,小小泳裤遮不住羞,只有逃跑。唉,逃得太慌忙,脚尖不慎触到地上的蒸气嘴,烫痕至今未愈。
马黛茶
多年前阅读博尔赫斯的小说的时候,发现小说中的人物动不动就在喝一种叫做马黛茶的玩意,而且这种玩意多和流浪的生活、沉默而倔强的性格、混乱的黑社会冲突以及没有盼头的恶时辰联系在一起,于是心神往之,虽不知其究竟为何物,但已然在心中把它看作典型的悲情拉丁符号。事实果然如此,在我几年前学习西班牙语的时候,发现任何一本关于拉美的读物都会不厌其烦地讲述马黛茶对于南锥体国家的重要性。但是直到来到巴西,我才真正品尝到马黛茶的滋味。
第一次请我喝马黛茶的是一个叫做Max的青年教师。在我请他喝完中国绿茶之后,他大叫不过瘾,旋即钻进自己的屋里拎出了一堆家什摆在我面前,说要我喝点来劲的。这些家什大致包括一根牛角、一包碎叶子和一把中间有吸孔的木勺子。他把碎叶子弄进了牛角,加上了水,用勺子捣鼓了半天,自己先爽了一口,然后递给了我。我吸了几口,其味果然美妙。问他此为何物,答曰,ervamate。由于葡语的发音怪异,音节te的发音相当于西班牙语里的chi,我半天过后才反应过来,我刚才喝的原来就是心仪已久的yerbamaté,马黛茶。
认识了葡文里的ervamate之后,我发现在任何一个冷饮摊都有一种牌子叫做leo(狮子)的加糖马黛茶饮料卖,就像加了糖的康师傅绿茶在中国满地都是一样,对于不能喝酒也喝不惯可乐的我来说,这种冷饮成了我在巴西利亚泡酒吧的最佳选择。
在我自以为已经识得马黛茶个中滋味的时候,“树皮艺术家”古斯塔沃狠狠地打击了我。我在前面的文章已经提到过,此君来自巴西和乌拉圭的交界处,而乌拉圭和阿根廷的马黛茶是全世界最正宗的。古斯塔沃认为leo是狗屎,Max的牛角也是小儿科,因为Max虽然也来自巴西南部,但那个州离阿、乌两国都甚为遥远,他们的牛角马黛茶就像东北人学做重庆水煮鱼一样,很不地道。
古斯塔沃隆重地从他随身携带的包里请出了他走到哪里都不能离弃的马黛茶具,那一刻之神圣,颇有大拜灶王爷的意思。我眼前果然一亮——乌拉圭人的家什比Max的牛叉多啦!一个陈年干葫芦壳做的茶壶,茶壶外面罩着精美的牛皮护套,带吸孔的勺子是纯银的,底端有过滤网,顶端郑重地刻着古斯塔沃的名字,另外,还有一个纯银外壳的小开水壶。古斯塔沃把一包看上去远比Max的碎叶子碧绿、清新的马黛茶叶末放进茶壶,用勺子把茶叶在壶中像火锅的鸳鸯锅一样分成两边,一边空疏,一边致密,然后加水,从空疏的一边开始喝,茶味慢慢淡下来之后,又从致密的一边把茶叶匀过来。茶味的复杂、舒爽和神异难以形容,喝了之后,我的确认为以前喝到的都只能算是马黛茶的盗版的盗版。(后来我才知道,古斯塔沃泡的是南大河州的chimarro,热水马黛,Max泡的是马托格罗索州的冷水马黛,没有正宗与盗版之分。)
那天喝马黛茶的时候,还有古斯塔沃的几个亲戚和几个来历不明的女性在场,像吸大麻一样,古斯塔沃请每个人轮着用同一把勺子吸茶水喝,直到茶味全部消失。开始我还觉得不习惯,后来才知道这是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巴西南里约格兰德州的风俗:善待朋友的最好方式就是拿自己的马黛茶具让大家轮流喝。
茶过三巡,古斯塔沃告诉我他们家乡的人祖先都是高乔人,马黛茶是他们的命根子,每个男人成人的时候都会得到一套刻有自己名字的马黛茶具,一生都不得丢失。我立即兴奋无比:终于和传说中的高乔人套上近乎了。高乔人被认为是南美的牛仔,他们由数百年前的西班牙逃兵、犯人和印第安女俘通婚而形成,远离城市,在潘帕斯草原上套马、宰牛、抢劫,藐视一切法律和私有财产。典型的高乔人一般头戴西班牙帽、身披印第安斗篷、穿着肥大的灯笼裤、腰间一边是弯刀一边是马黛茶具。他们一度被认为是潘帕斯草原动荡的根源,但后来就被奉为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数国民族性格的渊源。我告诉古斯塔沃,我读过何塞·埃尔南德斯所著的高乔民族史诗《马丁·菲耶罗》,古斯塔沃和他的亲戚们全都激动起来了——原来埃尔南德斯的某一处故居就在他们那个镇上。这帮高乔后裔齐刷刷地背诵起《马丁·菲耶罗》的开篇部分,又敲桌子又跺脚,那神情仿佛回到了祖先的马背上,桀骜、悲壮地喋血拉普拉塔河……
人民的芒果人民吃
早上起来,腹中空空欲进食,打开冰箱一看,居然任何吃的都没剩下。这两天新年假期,超市还不开门,怎生是好?我只有站在窗口发呆,抽支“早饭烟”聊以打发肠胃。这时,我突然发现窗外的芒果树下走来哲学教师若奥一家的男女老少,每人从地上拣起一个自行落地的芒果,朝果实累累的树上奋力砸去,每每砸中,必有数个丰满成熟的芒果应声落地,人民群众立即拾将起来,就地啃食。
靠!我真是饿糊涂了,怎么就忘了周围密密麻麻的芒果树了呢?这些天芒果开始熟了,正是大肆饕餮的好时机啊!但是……这玩意是可以随便啃食的吗?万一是私家种植的,临走前因为偷芒果坐进班房可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我朝楼下喊话:“唉,老若奥,这芒果树是你家种的吗?”“不是啊。”“不是你丫瞎吃什么的,不怕被抓啊!”“傻了吧,这周围的几百棵芒果树都是公共的,每年芒果一熟大家都来吃几嘴,不然白白烂掉了多可惜啊!”“我靠,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啊,我正愁没早饭吃呢!”“都一样,俺们也是没早饭吃了,这不,全家都来吃芒果来了。人民的芒果人民吃嘛!”我立即飞奔下楼……
为了不和若奥一家的芒果利益发生冲突,我选择了另一片芒果林。看来这儿的芒果真是多得人民群众都吃不过来了,很多离地仅一两米的枝条上活泼可爱的芒果都没人光顾。俺家周围的芒果不是俺们国内常见的那种熟了以后呈屎黄色的那种,全是一水儿的青芒,熟了以后果皮依然青翠,只是有些红晕而已。这种青芒最好吃,甜甜的脆脆的,质感味觉均为上乘。我顺手从最低的一根枝条上揪了一个貌似成熟的芒果,没想到揪下来之后,从果蒂上的断口突然喷出一股粘稠的白浆,仿似西班牙影片《乳房与月亮》里的美乳少妇狂喷乳汁一样,喷了我一身。此时,数学教师马努艾尔刚好走过我身边,他哈哈大笑说:“哥们儿,摘错了吧!还在喷浆的一准儿没熟,营养还没被果肉吸收好呢。”我拿小刀切开这个喷浆芒果一尝,果然,这家伙虽然果皮已然泛红,但味道奇酸无比,根本就没熟。马努艾尔教我摘向阳枝头的芒果,因为芒果的成熟需要充足的日晒。在他的指导下,我终于摘到了成熟得寂寞难耐的良家芒果若干,用迫不及待的舌头犒慰它们在无人问津的枝头上荒废的青春。
几个芒果下肚,俨然已经饱了。我正欲离开芒果林的时候,发现懒觉之后刚刚起床的邻居们都出来觅食来了,大家摘芒果的方法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政治学的里卡尔多教授勒令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爬上相邻的两棵芒果树大搞“摘芒果大赛”;语言学教授娜塔丽亚让她的大力士丈夫用力摇撼一个不算粗大的芒果树,自己在树下摊开吊床接落下来的果子;物理教授米盖尔和其他人相比简直是一个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类的天才,他发明了一种“精确制导”摘芒果工具,在一根长竹竿上绑了一个去了底儿的大可乐瓶子,看中了哪个芒果就将竹竿伸将过去,拿可乐瓶子将其罩住,然后稍事抖动竹竿,果子就落进了瓶子里,避免了落到地上砸得稀烂的惨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