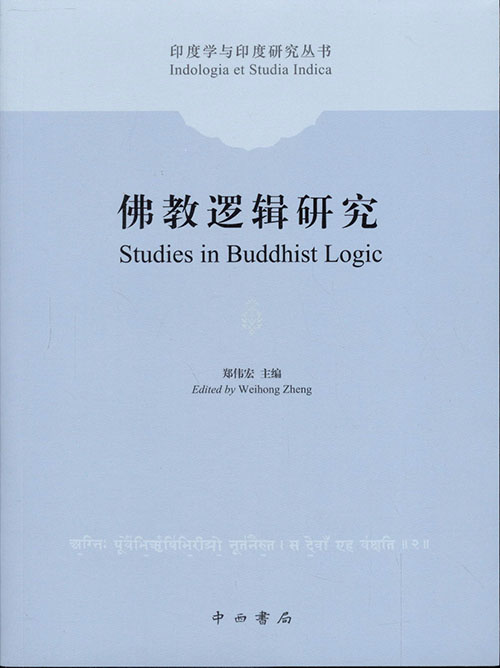《印度学与印度研究丛书:佛教逻辑研究》:
本来,在《理门论》内部是没有什么矛盾的。同、异品除宗既然使得因三相不能保证必然推出宗,那么就应实事求是地承认陈那新因明不是演绎逻辑,仍然停留在类比推理的阶段。
《研究》说:“建立因三相,是为了保证宗正确,第二种定义(同、异品除宗)使因三相不能保证宗的正确,因三相也失去了意义。”这一说法也值得讨论。
要知道古因明也有因三相,古因明五分作法是类比推理,我们不会因为它的结论是或然的就说五分作法“失去了意义”,同样不能认为古因明之因三相“失去了意义”。
陈那新因明之因三相虽然不能保证宗的正确,但也是有意义的。它避免了处处类比和无穷类比,提高了类比推理的可靠程度,这就是意义,而且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意义。
“为了保证宗的正确”(必然证成宗)只是主观的愿望,能不能必然证成宗,要依照逻辑的格来检验。陈那的因三相不能必然证成宗,不需要后人来承担责任,也不需要后人去修改它,提高它。逻辑史的研究是要还其本来面目。陈那认为,遵守其因三相规则,宗就能确认为真,即能“生决定解”,换句话说,能取得辩论的胜利。这是他的逻辑眼光,他的逻辑水平。这样的逻辑水平在印度那时代是领潮流的。作出演绎逻辑的评价,只是《研究》作者的主观想法,两者要分清。
五、以除宗有法为基础的同、异喻
《理门论》说:“又比量中唯见此理,若所比处此相审定,于余同类念此定有,于彼无处念此遍无,是故由此生决定解。”这一段话是说因三相是三支比量的因的规则、内容和作用。在一个比量中,因只有这三种相,不能多也不能少。“若所比处此相审定”是第一相“遍是宗法性”,“所比”指宗有法;“于余同类念此定有”是第二相“同品定有性”,“于余同类”是指宗有法之余与所立法同类的对象;“于彼无处念此遍无”即第三相“异品遍无性”。在陈那看来,遵守了因三相规则就能确认宗。
《理门论》告诉我们,因的三相是独立的,不能缺少任何一相。少了第一相就会出现四不成因过;少了第二相就会有不共不定因过;少了第三相就有共不定因过;第二、第三相同时缺少就成为相违因过。
沈剑英先生在断言“因的第二、三相是等值的,”“可任意舍去其一”。此说与《理门论》基本理论矛盾。九句因中的第五句因同无、异无,实例是“声常,所闻性故”,“所闻性故”因“一向离故”,只是少了一相,即不满足第二相“同品定有性”。如果第二、三相等值,那么等于是说第五句因同时不满足第三相“异品遍无性”。这显然与九句因理论相矛盾。第五句中的异品无因是满足第三相的。
如果第二、第三相等值,则所有的共不定因即第一、第三、第七和第九句因本来只是违反第三相“异品遍无性”的,按沈先生的解释也就同时违反了第二相“同品定有性”。这与九句因中的这四句不定因原本满足第二相相矛盾。
本来,第五句因只违反第二相,四种共不定因只违反第三相,它们是有区别的。如果说第二、三相等值,岂不是说四种共不定因与不共不定因也没有差别了?这显然又与陈那九句因理论矛盾。
总之,如果承认第二、三相等值,则违背其中一相就同时违背另一相。九句因告诉我们,四、六两句相违因是同时违背第二、三相的。这样一来,所有的不定因(四种共不定和一种不共不定)就都成了相违因,九句因实际上变成了只有两类:正因和相违因。这显然与陈那把九句因分成三类不符。这三类是:正因、相违因、不定因(四种共不定,一种不共不定)。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