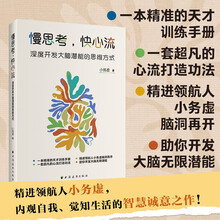康德曾从哲学的层面提出了如下四个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以及“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系列既涉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又以人自身之“在”为指向。儒学固然没有以康德的方式提出如上问题,但人的存在同样构成了其思考的中心。与康德以“人是什么”为逻辑归宿有所不同,儒学将“何为人”作为追问人之“在”的出发点,并由此进而展开了“为何在”、“向何在”,以及“如何在”的思与辨。
一
在儒家那里,“何为人”的追问,以广义的天人之辩为其背景。在提到人的存在处境时,孔子曾提出: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鸟兽”作为自然境域中的对象,属与“人”相对的“天”,“斯人之徒”则是超越了自然状态,具有文明特征的“人”。鸟兽不可与同群,隐喻着人不能停留或限定于自然的状态,和“斯人之徒与”,则意味着以文明的形态为存在的当然之境。在这里,一方面,孔子将“何为人”的问题与“我是谁”的问题联系起来:“我”(“吾”)的定位和归属(我是谁)所指向的是“斯人之徒”(“何为人”);另一方面,人(“斯人之徒”)又通过与自然的对象(鸟兽)之比较和区分,展示了其文明或文化的内涵。“人”超越自然(鸟兽)的性质,规定了“我”(“吾”)的文明向度,“我”(“吾”)与自然(鸟兽)的疏离、差异(“不可同群”)则进一步彰显了“人”的文明特征。人的文明化特征不仅体现于天人关系,而且也表现在人自身的不同存在形态中,在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便可以看到这一点: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管仲曾事齐桓公之弟公子纠,后齐桓公使鲁国之人杀公子纠,管仲不仅未为公子纠赴死,而且担任了齐桓公之相。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曾对此提出了批评,孔子的以上评价,是对子贡等人批评的一种回应。这里重要的不是孔子对管仲霸业的赞赏,而是对其社会历史贡献的肯定。“被发左衽”是所谓“夷狄之俗”,它隐喻着人的前文明的存在形态。在孔子看来,管仲的历史贡献就在于通过运用社会政治的力量,担保了文明进程的延续,避免了停留或回到前文明(“被发左衽”)的存在形态。相对于文明价值的维护,是否效忠于某一政治人物并不足道。从“何为人”的维度看,“我”(“吾”)之避免“被发左衽”,与“民之受赐”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的实质内容则是获得或维护文明的品格。这里既可以再次看到“我是谁”与“何为人”之间的相通性,也不难注意到对人的文明规定的确认。不妨说,“何为人”的追问,在此具体化为对文明及文化的认同;儒家所展开的夷夏之辩,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体现了以上主题。孔子所体现的上述儒家视域,与道家显然有所不同。较之儒家之注重人禽之别,道家似乎趋向于模糊人与其他对象的界限。《庄子》在描绘“至德之世”时,便将同于禽兽居视为其特点:“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至德之世”是庄子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态,同于禽兽居则意味着文明价值的消解。从天人之辨看,庄子似乎多方面地表现出对文明进程及文明成果的疑惧、责难。对他而言,自然的形态是最为完美的,而文明的演进则总是导向自然形态的破坏,所谓以“人”灭“天”。这样,与儒家要求超越自然不同,道家更多地倾向于以“天”(自然)规定人。庄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便是所谓“天人”:“不离于宗,谓之天人”。这里的“天”作修饰词或限定词用,所谓“天人”,也就是合乎天或自然化的人。在“鸟兽不可与同群”与“同于禽兽居”、避免倒退到前文明形态(“被发左衽”)与回到前文明形态的分野之后,不难看到儒道对“何为人”的不同理解。作为文明化的存在,“斯人之徒”同时呈现类或社会的特点,与“被发左衽”相对的文明形态,也表现为社会的产物,与认同文明的价值相应,儒家对人的社会品格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孔子的学生曾参曾作过如下自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人”、“朋友”泛指自我之外的他人,“传”则是前人思想的载体,三者分别从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活动及文化传承等方面体现了“我”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在这里,反省的主体是“我”(“吾”),然而,反省的对象则指向“我”(“吾”)之外的他人(现实交往中的人与“传”所涉及的历史中的人)。“自省吾身”在相当意义上体现了自我的认同(self-identity),但在以上的逻辑关系中,自我的认同却以社会的认同为其内容;这种思维进路所确认的,是人的社会归属或类的规定。对人的社会归属或类的规定的关注,在孔子关于朋友的看法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孔子很注重朋友间的关系,曾从不同的方面提到或论及朋友的存在意义。对孔子而言,朋友的特点在于志同道合,后者不仅仅限于私人间的趣味相投,而且更表现在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里的“乐”,是与志同道合者相处、交往时产生的内在愉悦,这种交往、相处乃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相近的理想追求。与此相反相成的,是“毋友不如己者”。此处的“如”,有“类”之意,“不如己”,犹言“不类己”;与之相应,所谓“毋友不如己者”,并不是拒绝与社会地位或人格修养等方面比不上自己的人交友,而是指不要与缺乏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己不属于同一类)者为友。不难看到,在这里,孔子所侧重的,仍是社会的认同:与己同类者(志同者)友之,与己不同类(非志同者)则远之。同样的观点也体现于人物的评价上。《论语?子路》曾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的如下对话: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亦即为善者所肯定,为恶者所否定,它所体现的也是类的认同。如果说,朋友之伦是从特定的社会关系上确认了人的社会认同,那么,“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则似乎从更广的层面上表现了人之以类相属或以类相分的社会品格。以人文化、社会化为内在规定,人既有求知的能力,又具有求知的要求。《论语》首篇第一章,便将人之“在”与“学”联系起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这里的“学”,便包括广义的“知”。孔子很注重“知”,并把“知”(智)视为超越迷惑、达到自觉的前提。所谓“知者不惑”,便表明了这一点。同时,孔子以“仁”为其学说的核心,而仁即以“知”为题中之义:“未知,焉得仁?”如果不辅之以“学”,则“仁”便将呈现消极的意义:“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仁道所肯定的,是人的内在存在价值,“学”则以理性的自觉为指向;仅仅具有人文的观念而缺乏理性的自觉,往往易于导向自发与盲目(所谓“愚”)。仁与知的以上统一,意味着人同时应当是一种理性的存在。孔子曾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回顾,并自述如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学”是对已有的文化、认识成果的把握和接受;“立”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有所成就,它的更实质的涵义是行为合乎礼义规范,从而能挺立于世;“不惑”表现为明辨是非,并作出正确判断;“知天命”以理解与把握历史的必然之势为指向;“耳顺”与逆耳相对,表现为以宽容的精神对待别人的意见(听到不同意见,亦不觉逆耳);“从心所欲”即行为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不逾矩”则是遵循普遍的规范,二者的统一,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之境。在这里,“学”或“知”构成了极为重要的环节:三十之立、四十之不惑,以“志于学”为前提;六十之耳顺、七十之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奠基于“知天命”。上述过程当然并不仅仅是孔子对个人一生的自我反省,它所涉及的,乃是普遍意义上人的成长与“在”世过程。通过肯定“学”与“知”对人“在”过程中的意义,孔子同时也进一步突出了人的理性规定:正是“学”与“知”所内含的理性品格,使人由本然的、自在的形态,提升为自觉的存在。在儒家那里,理性的自觉往往与道德实践联系在一起,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首先便表现为道德行为的特点,而知命则以成为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为目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知”是以理性的方式来把握,“天命”则是当然之则的形上化(人的使命、职责被赋予必然的性质);惟有将当然(人的使命、职责)作为必然来理解和把握(知天命),才能成为道德意义上的存在(“君子”)。对儒家而言,履行道德或伦理的职责,是人的基本使命。人之为人,便在于能自觉地承担这种职责。在对隐者的批评中,这一点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隐者虽存在于社会之中,但却试图从社会伦理责任中解脱出来,这种仅仅追求个人的洁身自好而悬置社会伦理责任的趋向,显然未能注意到伦理关系对于人之“在”的内在意义。通过对伦理职责与伦理关系的如上强调,儒家同时肯定了人是伦理的存在。伦理的规定与人化(文明化)、理性化等向度,更多地体现了人的“类”或社会品格。然而,作为具体的存在,人又包含个体之维,而并不仅仅表现为“类”的化身;在肯定人是理性的、社会伦理的存在的同时,儒家对人的个体性规定也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注。孔子曾提出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指向的是个体自身的完善,为人则是对他人的外在迎合,对“为己”的肯定,显然内含着对个体存在价值的确认。就道德实践的过程而言,个体同样构成了主导的方面:“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为仁既指按仁道的理想自我涵养或自我塑造,也指在行为过程中遵循仁道的规范或原则,而二者都主要依赖个体自身。人所内含的个体性品格更具体的体现于个体与“众”的关系之中。《论语?卫灵公》有如下记载: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众”与个体或自我相对,众恶、众好,表达的是众人的意见与态度;众恶之必察、众好之必察,意味着对众人的意见与态度加以进一步的反思与考察,而反对盲目从众;这里既体现了一种理性的立场,也蕴含着对个人独立性或自主性(个体独立地看待问题、自主地作出判断)的肯定。与之相联系的是对“乡原”的批评:“子曰:‘乡原,德之贼也。’”“乡原”即乡愿,其特点在于迎合世俗之意、缺乏独立的判断与担当意识,所谓“同流合污以媚于世”,在与世俗的“同流合污”中,个体本身往往也被消解。可以看到,乡愿之所以为德之贼,不仅在于其拒绝坚持原则,而且也在于其导致个性的丧失。反对从众、拒斥乡愿,主要以否定的方式突显了个体的不可忽视性,在积极的意义上,个体的关注则体现于对人的个性差异的尊重。以教育过程而言,孔子非常注重教育对象的个性特点,并要求个体不同的特点而给予相应的引导。《论语?先进》记载: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诸’。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这里涉及的是广义的知与行的关系:了解、把握了某种义理,是否应该立即付诸实践?对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孔子没有给予笼而统之的解答,而是针对提问对象的不同特点,作出不同的回应:对率性而行的子路,以“父兄在”加以约束;对性格较为谦退的冉有,则以“闻斯行诸”加以激励。从教育学的角度看,这里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就人之“在”而言,其中无疑又蕴含了对个体性规定的确认。以天人之辩为出发点,孔子首先将人置于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肯定了人不同于自然的人文化(文明化)、社会化品格,后者进一步展开为理性的、伦理的规定。与人化(文明化)、理性化、伦理化等相辅相成的,是人的个体性规定。以上诸方面的交融和统一,展示了儒家对“我”是谁与“何为人”的具体理解,而这种理解,同时又构成了儒家思考与回应“为何在”、“向何在”、“如何在”的逻辑前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