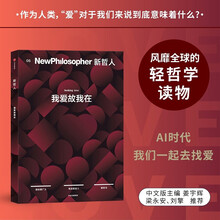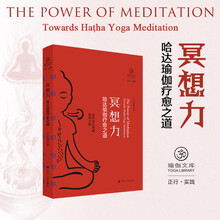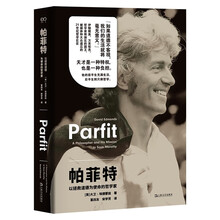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对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进行了诅咒,在这些诅咒中,维特根斯坦认识到的“真理的部分”是哪一部分?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才是维特根斯坦的基督教,以至于尽管有这么个“真理的部分”,他还是被那位都灵发狂者·的反教士法规所深深伤害?这些是关键性问题,只要我们意识到,尼采和维特根斯坦,在这一百年里,以对哲学进行哲学式藐视的某种特定形式,先后给出了自己的招数。
2
尼采与维特根斯坦共享的这部分东西,我们用“反哲学”这个词来指代,它是这一百年里第三位伟大而迷人的诋毁哲学者——雅克·拉康引入的。这个词不够严谨,但是并不孤立,因为如果弄清这个词是当下这个文本——维特根斯坦将在其中担任我们的老师——的关键所在,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界定它的力量范围。
反哲学,从它的源头开始(我是想说自赫拉克利特开始,他是巴门尼德的反哲学家,就像帕斯卡是笛卡尔的反哲学家一样),就可以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运作来确认:
1.对哲学陈述进行语言的、逻辑的、谱系的批判;对真理范畴的消解,对哲学自我建构为理论这一企图的瓦解。为此,反哲学家常常探寻智者学派也去探寻的源头。在尼采那里,这一运作以“重估一切价值”为名,反抗柏拉图式疾病,即符号与类型的战斗语法-。
2.意识到这一事实,即哲学最终不能归结为其论证的表象、命题以及理论的虚假外观。哲学是一个行动,围绕着“真理”的那些虚构只是外在的楚楚衣冠,是宣传和谎言。在尼采那里,涉及到的是在那些装扮之后辨别出教士的权力形象,那是反动力量的积极组织者,虚无主义的获利者,沉迷于怨恨的总管。
3.针对“哲学的行动”,召唤另一种极端的革新行动,它要么也被称作哲学的,由此创造了一种含糊其辞(通过它“小哲学家”愉快地赞同着吐在自己身上的唾沫);要么更诚实地被称作超一哲学的,甚或去一哲学的。这个前所未有的行动在阐释哲学行动的损害性的同时,也摧毁了哲学行动。它毫不犹豫地克服了它。在尼采那里,这个行动的性质是极端政治的(archi—politique),其指导方针是:“把世界历史劈成两半。”
我们可以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发现这三个运作吗?在这里,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是一个仅有的文本,是他认为唯一值得公开出版的文本:《逻辑哲学论》。其余的,所有其余的文本,只适合说(考虑到其中的一切均渐渐支离破碎)仅仅具有内在注解的地位,一部个人的《塔木德》而已。当然,对于本段开头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
1.哲学被解除了所有的理论自负,并非因为它将因此而成为含混和错误的编织物——这么说仍然是作了太多让步——而是因为它的意图本身变得无效:“关于哲学问题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T.4.003]反哲学的典型特点即,它的目标绝不是争论任何哲学论题(就像当得起“反哲学”之名的哲学家反驳其前辈和同侪时所做的那样),因为要这样做就必须和他们共享一些标准(比如真和假)。反哲学家想做的,是在谬误及有害的维度上,整体性地确定哲学的欲望。疾病的隐喻绝不会在这一计划中缺席,而且它当然是来自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无意义”。如果“无意义”就是指“被剥夺了意义”,那么就意味着,哲学甚至不是一种思想。思想的定义则是确切的:“思想是具有意义的命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