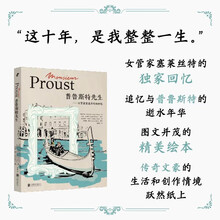阿特伍德成长的多伦多是个思想保守,带有清教色彩的城市:禁止开设路边咖啡馆,公共节日几乎为零,市政法甚至禁止人们在后院喝啤酒。20世纪50年代末,多伦多开始发生一些质的变化,一场文化革命有声有色地展开了。新的爵士乐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民谣现象渐渐在一些地方抬头,贝街的汉堡之家和阿斯奎思街一间旧马车房里的一楼俱乐部中聚集了一批文化逃避者……在这种激情萌动的氛围下,1960年6月1日,在杨街西面的一间仓库里,波希米亚使馆开张了。
波希米亚使馆并非真正的使馆,尽管偶尔会有人写信咨询办理签证事宜,给这处地方增添了一丝神秘气息。波希米亚使馆创办人唐·卡伦年纪不到三十岁,是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新闻部的一名文书,职责是撰写周日晚间国内新闻报道。当时广播公司员工午餐时间大都聚在贾维斯街的名人俱乐部,吃吃喝喝,谈天说地。卡伦的想法是创办一个可以替代名人俱乐部的无酒精夜间俱乐部。电视新闻部的五位员工每人出资一百加元,波希米亚使馆诞生了。卡伦在大学街的伊顿百货买了两套附带十四个杯子的铝制渗滤式咖啡壶和一个电炉,并印制了广告传单,前往大学体育场的足球比赛场地,一边分发传单一边宣传:“您想来点颠覆式文学吗?”
波希米亚使馆是一间私人俱乐部。由于警察不喜欢这种工作时间之外的聚会,他们试图关闭这地方,听众席里时不时会出现便衣警察,但波希米亚使馆从不售卖酒精饮料,也严禁在场人员吸毒,因此警民之间相处还算和谐,俱乐部在有惊无险中开办了下去。
俱乐部营业时间是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基本上每晚都有固定安排,其中周四是文学夜,周五是民谣夜,周六是爵士夜。波希米亚使馆定期上演时事讽刺剧和即兴喜剧,它的长处在于什么都涉足,而且大力扶持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让·热内的《女仆》在这里举行了北美首演,大卫·弗伦奇和大卫·弗里曼的首个剧本都是在这里上演的。
不久,波希米亚使馆便声名鹊起,很多人慕名前来,其中包括莱昂纳德·科恩和亨瑞·贝拉方特。丹尼斯·李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俱乐部的报道,把那些消息读给阿特伍德听,阿特伍德对这种非多伦多特色的文化现象很感兴趣,两人结伴前往,听了爵士乐、民谣和诗歌。阿特伍德发现,里面的听众大多是些把音乐和诗歌看作逃避“没落资产阶级和体面工薪束缚”的青少年。对于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个令人陶醉之地。
波希米亚使馆为多伦多作家提供了一个场所,大家第一次有了可以聚在一起畅谈文学的地方。由于当时大多数人写诗,写小说者寥寥无几,所以聚会时也多以读诗和谈诗为主。1960年11月,阿特伍德首次在俱乐部公开朗诵诗歌。在她的记忆中,这是场噩梦般的经历。虽然她在维多利亚学院有过多次舞台表演经验,从未怯过场,在这里,她却觉得自己像个新手,完全暴露在大家的视线里,“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会场里,人们走来走去,有的去拿咖啡,有的在咖啡机上忙活,有的在说话。她在台上面色苍白,恶心反胃。她事后评论道:“如果你能在波希米亚使馆挺过来,你就能在任何地方朗诵。就在你读到(诗中)最哀伤之处时,肯定会有人在这时冲洗马桶或者开动咖啡机。”但不管阿特伍德自己感觉有多糟糕,却有不少人开始关注这个戴着角质架眼镜的年轻女子,他们感到她身上有种不可忽视的力量,那是一种洞悉一切的智慧。
波希米亚使馆是个广阔的天地,是阿特伍德在校园之外最喜欢逗留的地方之一。她在此结识了很多人,他们在日后都成了她的挚友,使她受益匪浅。年长一代的人里有杰·麦克弗森、菲利斯·韦伯、艾尔·珀迪和玛格丽特·阿维森,年轻一代的人里有格温德琳·麦克尤恩和大卫·唐奈儿。他们的圈子不大,但思想开放,有才华者皆可加入。
然而,即使是在波希米亚使馆这样一个充满叛逆和颠覆精神的俱乐部里,阿特伍德依然能够嗅到一丝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气息:针对女性的伪善态度。从俱乐部各种宣传中透露出的信息都在表明,创造力是男人的专属,女人在多数情况下只是陪衬。一个女人如果不想被打发到女粉丝的行列中去,就必须小心翼翼,并且得加倍努力。
阿特伍德第一次在俱乐部朗诵诗歌时,当时小有名气的爱尔文·莱顿就坐在听众席里,他用大家能听得见的声音诵读起自己的诗歌,读完立刻睡着了,大声打起呼噜。后来只要有阿特伍德在场的时候,他便会像只公鸡似的竖起羽毛,仿佛能感知危险。有一次,阿特伍德在晚宴上遇见莱顿,他宣称阿特伍德的好友、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维森“看起来鬼鬼祟祟”,因为她知道自己在侵犯男人的领地。阿特伍德心里明白,莱顿其实是在宣告,不是女人不能写诗,而是她们根本不应该写诗。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