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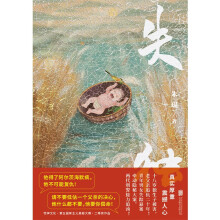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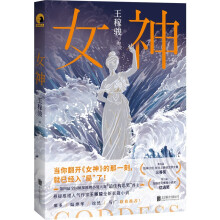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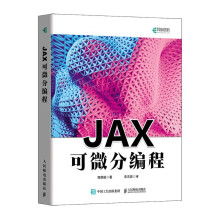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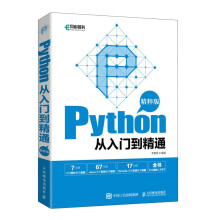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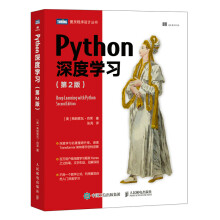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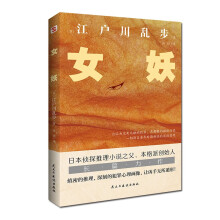
◆地球上40亿年来zui重要的10件事:DNA、光合作用、眼睛、性等的进化决定了你今天的样子。
◆没有氧气,生命只能停留在细菌等级;复杂细胞使生命不可避免地变得复杂;性让*好的基因组合出现在一个个体身上。少了其中任何一次,你都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样子。
◆《生命进化的跃升》曾获得2010年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2002年《果壳中的宇宙》获得该奖,2004年《万物简史》获得该奖)。
◆《新科学家》《自然》《泰晤士报》和《独立报》评选它为年度图书。
◆ 《独立报》称莱恩为“我们时代zui令人激动的科普作家之一”。
◆翻开本书,见证你本身就是40亿年来亿万分之一的奇迹。
40亿年前,海底热泉偶然地成为你和其他生命的起源之地;
之后,DNA的复制密码让你得以繁衍;
直到光合作用制造出氧气,你才解决了能源问题;
接着,复杂细胞让你的构成从简单变为复杂;
有性生殖打乱了遗传组合,让你结合父母的有点;
运动扩大猎食范围,让生存变得容易;
眼睛成为你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
热血提升新陈代谢速率,以维持你的大脑消耗;
意识更是让你得以学习、思考以及成长;
直到生命尽头,你会发现死亡才是一切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总而言之,在地球上,生命已经进化了40亿年。但与达尔文猜测的不同,进化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顺理成章地向前滚动;而是在某个时间点忽然跃升,激进地一路狂奔。DNA、光合作用、眼睛、性等10次进化,少了其中任何一次,你都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样子。
翻开本书,见证你本身就是40亿年来*大的奇迹。
生命进化的跃升:第五章 性——地球上最伟大的彩票
所以现在很清楚,有性生殖所做的事,就是混合基因产生新的排列组合,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组合。它会在整个基因组上不断地系统性地做这件事,就像洗一副扑克牌,打破之前的排列组合,以确保所有的玩家手上都有公平的牌。但是问题是,为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最早在1904年由德国的天才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解答,他提出了一个现在依然让大部分生物学家觉得十分合理的答案。魏斯曼可以算是达尔文的继承者,他主张有性生殖可以产生较大的变异,让自然选择有更多作用机会。他的答案和达尔文十分不同,因为他的答案暗示性的好处并不针对个体,而是针对群体。魏斯曼说,性就好像乱丢各种“好的”和“坏的”基因组合。“好的”基因组合让个体直接受益,“坏的”基因组合直接伤害个体。也就是说,对于任一世代的个体而言,性并没有好处或坏处。但是魏斯曼认为,整个族群会因此进步,因为坏的组合会被自然选择消灭,最终(经过好几个世代后)会留下各种最好的排列组合。
当然,性本身并不会为族群引进任何新的变异。没有突变的话,性就只是把现存的基因组合打乱然后移走坏的基因,从而减少基因变异性。但如果在这个平衡中加入一些小突变的话,如同1930年统计遗传学家罗纳德·费希尔爵士所指出的,性的好处就变得非常明显。费希尔认为,因为突变的概率很低,所以不同的突变比较容易发生在不同人身上,而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两次。这道理就像两道闪电往往会打在两个不同的人身上,而不会两次打中同一人(但不管是突变或闪电,都有可能两次打中同一人,只是概率极小)。
后来,美国的遗传学家赫尔曼·穆勒在理论中导入了有害突变的影响。穆勒因为发现X射线可以引起基因突变,获得了1946年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他曾在果蝇身上引起数千次的突变,因此比任何人都清楚,大部分的突变都是有害的。对穆勒而言,有一个更深层的哲学问题徘徊于此。一个无性生殖的族群,如何逃离这种有害突变的影响呢?穆勒说,假设大部分的果蝇都有一到两个基因突变,整个族群中只有少数基因“干净的”个体,那会发生什么事?在一个小规模的无性生殖族群里,它们没有机会逃离适应度衰退的命运,就像永远只能往一个方向旋转的棘轮一样。因为是否有繁殖机会,依赖的不只是基因的适应度,还要靠运气,也就是说,要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假设现在有两只果蝇,一个有两个基因突变,另一个没有。如果突变的果蝇碰巧身处食物丰富的地方,但是“干净的”果蝇却不幸饿死,那么就算突变的果蝇适应度较差,却只有它的基因有机会传给下一代。这种情况可能一再发生,每一次都像棘轮旋转一格一样,最终整个族群将会衰退到无可挽回直到灭亡,这个过程现在称为穆勒棘轮效应。
而性可以解救这一切,因为有性生殖可以把所有未经突变的基因集中到同一个个体身上,重新创造出一个完美无瑕的个体。这道理就好像有两辆坏掉的车子,假设一辆的变速箱坏了,另一辆的引擎坏了,那么如英国进化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所说,性就好像修车师傅一样,可以把两辆车子好的部分拼成一辆好车。
在这个大公无私的有性生殖里,唯一可能打破公平的假说由机灵的俄罗斯进化遗传学家阿列克西·康德拉肖夫在1983年提出。他提出了关于有性生殖的非凡理论。这项理论有两个大胆的前提,不过这两个前提至今仍引起进化学者激烈的争辩。第一个前提就是基因突变的速度要比一般人想象的快。根据康德拉肖夫的假设,每一代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会产生至少一个以上的有害突变。第二个前提则是,大部分的生物都或多或少可以承受一个基因突变的害处,只有当我们同时遗传到许多突变的时候才会开始衰退。
那这两个假设如何帮我们解释有性生殖呢?根据第一个假设,也就是高突变概率,暗示了即使规模庞大的族群,也不能完全免于穆勒棘轮的影响,它们无可避免地会慢慢衰退,最后发生“突变引起的灭绝”。第二个假设则很聪明,因为它让性可以一次性剔除两个以上的突变。英国生物学家马克·里德利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就像《圣经》里面的《旧约》与《新约》一般,突变就像原罪。如果突变速率快到每一代都有一个突变(就好像每个人都是罪人),那么要除去一个无性生殖族群里的原罪,唯一的办法就是毁掉整个族群,不管是用洪水淹没他们,还是用硫黄烈火烧死他们,或者用瘟疫毁灭他们。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有性生殖的生物可以忍受数个突变而不受伤害(直到它们可以忍受的极限),那么性就有办法从表面健康的父亲与母亲那里搜集突变,然后全部集中到一个小孩身上。这就是《圣经·新约》的办法,耶稣为了所有人类的原罪而死,性也可以把全族群的突变累积到一个替罪羔羊身上,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牺牲掉。
引言
第一章 生命的起源——来自旋转的地球
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至今还在我们体内传承。诺奖得主杜维认为,从化学反应的本质来说,生命更应该在 1万年内诞生,而不是 100 亿年。虽然时间不确定,不过从化学角度来看,随着 38 亿年前的地球自转,生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第二章 DNA——生命密码
DNA 的双螺旋结构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科学,更神奇的是所有生命都使用相同的 DNA 编码,似乎表明在地球上,生命只诞生了一次。对于 DNA 结构的发现者克里克来说,这暗示了外星生物的一次播种,我们有更好的答案吗?
第三章 光合作用——太阳的召唤
光合作用产生氧气是件难以置信的事,因为不管在地球上、火星上或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光合作用都可以不依赖氧气进化出来。如果没有氧气的话,生命或许只能停留在细菌等级,而我们只是茫茫细菌世界里某种有感知的生物而已。
第四章 复杂细胞——命运的邂逅
没什么东西比细菌更保守了,主宰地球 30 亿年,自始至终都是细菌;也没什么东西比复杂细胞更激进了,引发了寒武纪大爆发,物种开始肆意创造。细菌进化为复杂细胞,似乎不像达尔文所说的渐进式,而更像一场命运邂逅引发的突变。
第五章 性——地球上最伟大的彩票
几乎所有的真核生物都会沉溺于性,无性生殖的物种大多走向灭亡。但有性生殖又那么古怪,它每次都像洗牌一样,打破之前的最佳组合,难道是为了确保所有玩家手上都有公平的牌吗?
第六章 运动——力量与荣耀
我们太熟悉运动了,以至于忽视了运动的重要性。是运动使我们能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点,这种生活给了动物目的,也让开花植物有了意义。而使运动成为可能的是组成肌肉的各种蛋白,谁能想到从这些蛋白质中还能看出我们和苍蝇的亲缘关系呢?
第七章 视觉——来自盲目之地
95% 的动物都有眼睛,眼睛也是对进化论最大的挑战,如此复杂又完美的东西,怎么能通过盲目随机的自然进化发展出来?追踪视网膜上的视觉色素,最终将看到眼睛的共祖和叶绿体的祖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八章 热血——冲破能量的藩篱
热血反应新陈代谢速率,而新陈代谢速率反应我们的生活节奏。如果我们想知道自身快节奏生活的原因,就要看到整个生命进化史,看到极端气候起决定作用的时候。那时哺乳动物的祖先在地下气喘吁吁,恐龙正称霸一方。
第九章 意识——人类心智的根源
我们总觉得自己的意识有些“非物质”,但当有了基本的情绪、动机、痛觉等知觉,其他的高级认知,如语言,都只不过是一堆复杂的脑回路,被设定在复杂的社会中工作而已。那我们的大脑是如何产生意识的呢?
第十章 死亡——不朽的代价
进化应该对个体有利,那我们很难理解死亡对我有什么好处。但想想癌细胞就可以明白,不死的细胞是有毒的,只有死亡才能造就多细胞生物。不过死亡的进化又像天上掉的馅饼一样,倾向于寿命越长,青春的时间也越长。
后记
致谢
参考文献
☆一个令人敬畏的原创故事。前两章是我读过的关于生命诞生这一话题zui连贯、zui令人信服的总结……这是一次生物学zui深刻、zui重要、zui令人振奋的思想之旅。任何对生命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强烈推荐。
——《新科学家》
☆一本好书,非常有趣,可读性强,充满热情,也不怕奇异的观点带来争议……把它当作枕边书是令人绝望的:你永远不会睡着。
——格拉汉姆•凯恩斯-史密斯,《化学世界》
☆本书提供了一个令人着迷的视角,它展示了科学家们如何以一种能与自然相媲美的创造性来理解进化论。
——《科学新闻》
☆如果达尔文从墓里复活的话,我会给他这一本好书,让他能够快点赶上进度。
——马特•里德利,著有《红色皇后》《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
☆作者从微观到巨观,对生命现象的来龙去脉做了非常清楚的交代,让我们对生与死有了另一番新的体悟。
——胡哲明,台湾大学生态学与演化生物学研究所副教授